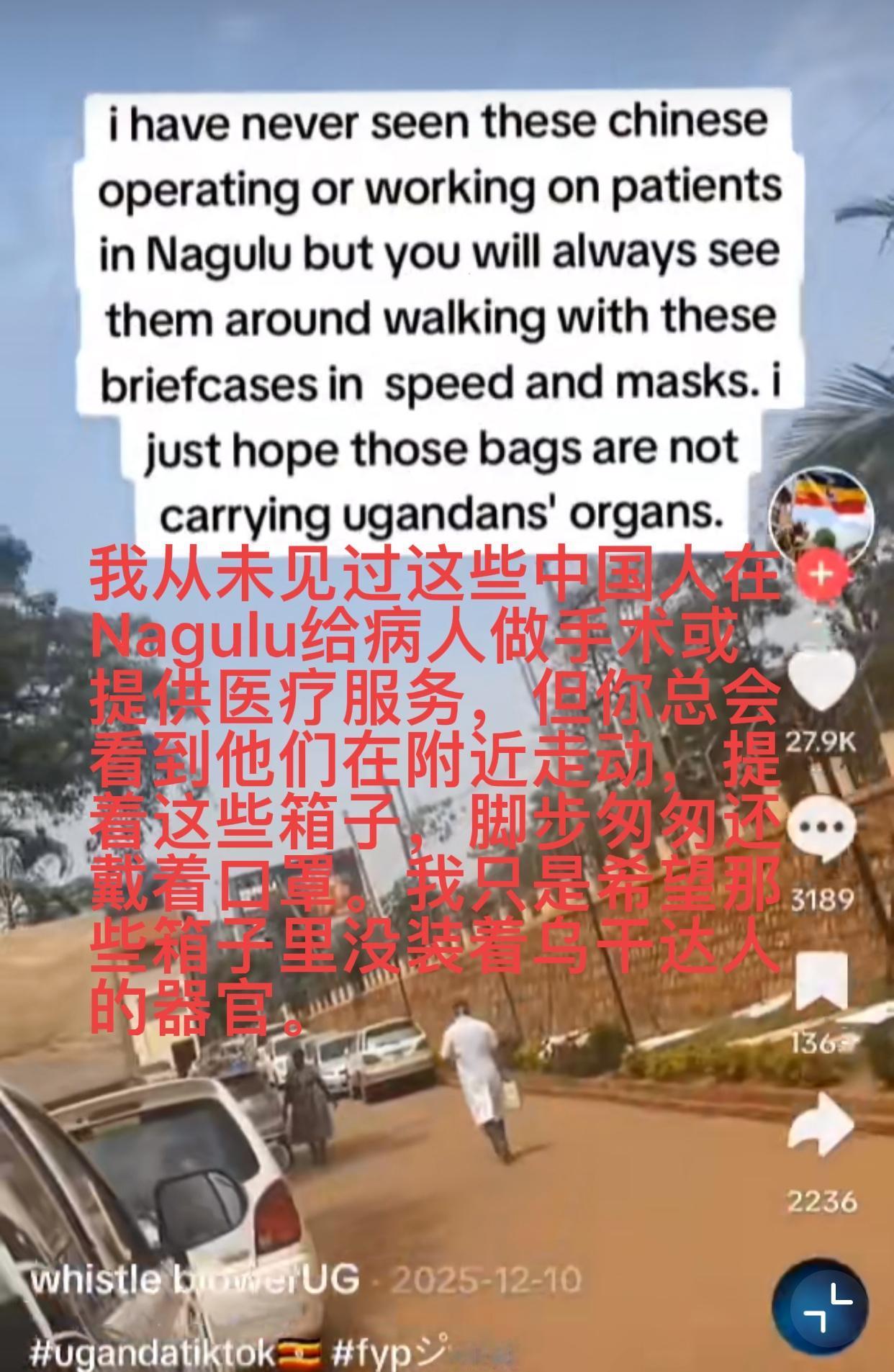同事乔迁请了全部门,唯独没请他!路边摊看到他后我做了个决定 晚上骑车拐过人民路,快餐摊的油烟混着孜然香飘了满街。我一眼瞧见那个熟悉背影——小王独自坐在矮塑料凳上,左手攥着烤串,右手划拉手机,屏幕的光打在他脸上,明明灭灭的。 “哎,你怎么在这儿?”我把电动车停在他旁边。 他抬起头,眼角好像抽了一下,笑得不太自然:“家里没开火,随便对付一口。”手里的烤鱿鱼转着圈,辣椒粉撒得有点抖。 我心里咯噔一下。今天全部门都去小陈新房暖房,上午办公室还热火朝天地议论买什么礼物。可现在小王坐在这儿,白衬衫袖口蹭了块油渍。 “小陈家今晚……”话到嘴边我刹住了。 他咬鱿鱼的劲儿突然狠了点:“没喊我。”油星溅到眼镜片上,“可能忙忘了吧,三十多号人呢。” 路灯啪地亮了,把他影子钉在地上。我想起上个月小王通宵帮他改方案,想起小陈儿子发烧那次,小王连着顶了他三天夜班。烧烤摊老板吆喝“羊肉串好嘞”,隔壁桌学生娃娃笑闹着抢竹签。 我摸出手机走到梧桐树下边。电话接通时,那头都是碰杯声和“乔迁大吉”的吵嚷。 “临时有点急事,真过不去了。”我碾着脚边的烟头,“礼物让老张捎去了,给嫂子添个喜庆。” 挂了电话,我冲老板扬扬手:“再加二十串肉筋,两瓶冰啤酒!”塑料凳腿在水泥地上刮出刺啦一声。小王愣愣地看着我坐下,啤酒瓶盖起开的“哧——”声,像谁轻轻叹了口气。 “这摊子我熟,”我给他倒酒,“大学那会儿每周五都来。”泡沫涌出来漫过手背。我们碰瓶时没说话,烤架上的火忽然旺起来,橙红的光在他脸上跳。 肉串凉了又热,啤酒空了两瓶。他说起老家房子去年翻新,母亲在电话里总问“和同事处得咋样”。说这些时,他把竹签一根根捋齐,码得整整齐齐。 夜市霓虹亮成一片时,他忽然开口:“其实我晓得为啥。”但话头在这里断了。结账时老板少算了十块,笑着说常来啊。 推车走时,秋风卷着糖炒栗子的焦香。他忽然拍拍我后座:“走了啊。”两个字散在风里,轻得像柳絮。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又压短,前面写字楼还有几扇窗亮着,有一扇是我们常加班的那间。 拐弯前我回头看了眼,快餐摊那簇火还烧着,在这越来越凉的夜里,暖烘烘的,怪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