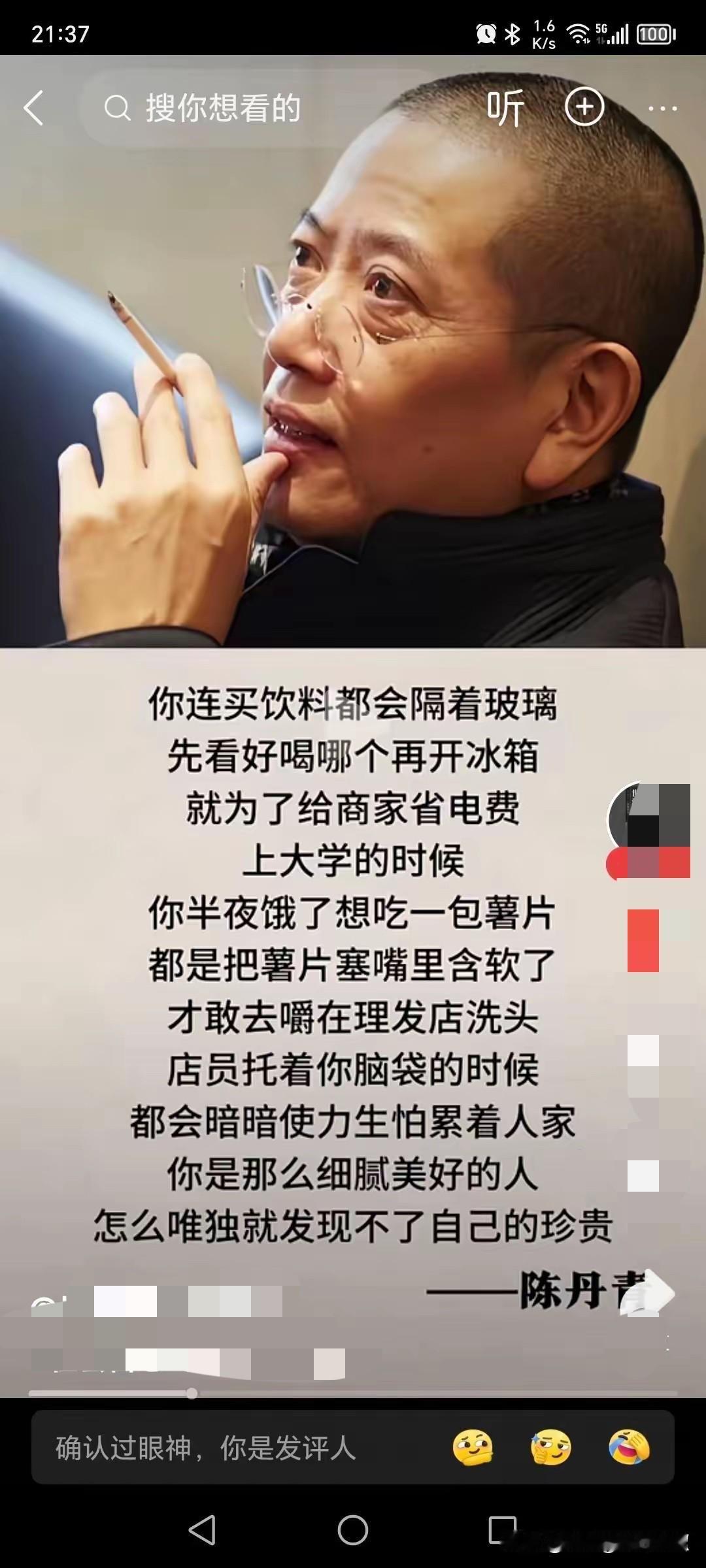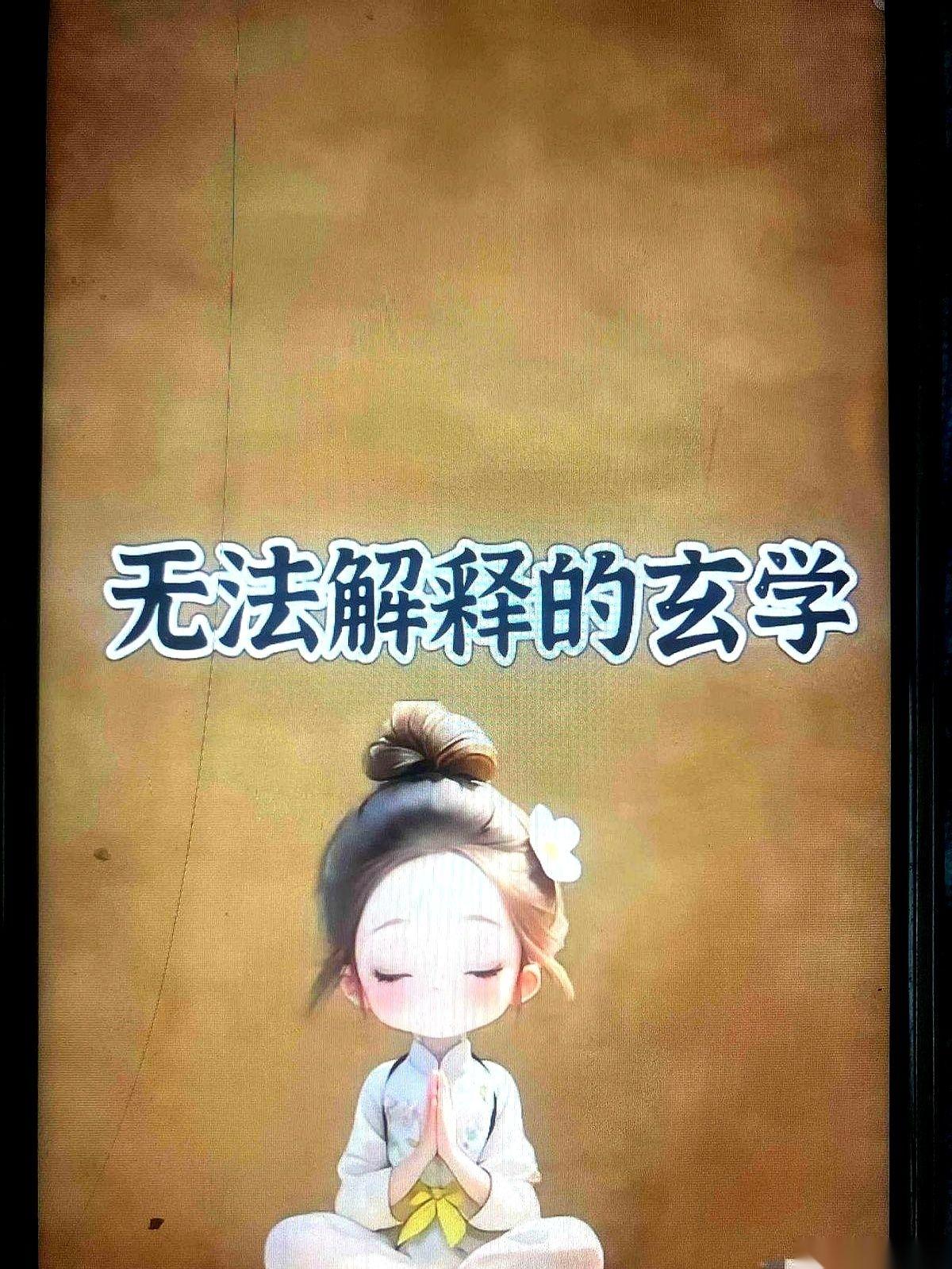我守着巷口的修鞋铺,已经十五年。铺子小,只够摆一张铁砧,两把锥子。男人早年跟人去南方打工,走时说混出模样就回来,这一走,音信全无。我靠着修鞋养大女儿,供她读大学。铺子门口的梧桐叶绿了又黄,鞋跟上的钉子换了一拨又一拨。这天,一个穿西装的男人站在摊前,皮鞋尖蹭着地面,有些局促。他递过来一双皮鞋,鞋面锃亮,鞋跟却断了一截。“师傅,能修吗?”他声音低沉。我接过鞋,指尖碰到鞋面的纹路,忽然顿住。这双鞋的内侧,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是当年他走前,我用锥子不小心划的。我抬头看他,鬓角已经发白,眉眼却还是当年的模样。“能修。”我低头,声音有些发颤。他没走,站在梧桐树下抽烟,看我一针一线地缝补。风卷着落叶,落在他的肩头。“师傅,”他忽然开口,“这鞋跟,得用最好的胶。”“放心。”我把鞋跟钉牢,又擦了一遍鞋油。他接过鞋,递过一张百元大钞,说不用找了。我把钱塞回他手里:“修鞋十五,多了不要。”他愣了愣,接过零钱,转身要走。“你回来,是为了啥?”我忽然问。他脚步一顿,没回头:“女儿要结婚了,回来送份嫁妆。”我手里的锥子,哐当一声掉在铁砧上。女儿昨天才打电话,说谈了个对象,对方家境殷实,就是父亲常年在外,母亲一个人守着个修鞋铺。“她不知道你……”我声音发涩。“不用让她知道。”他走远了,声音飘在风里,“这鞋,是当年你给我买的,我一直没舍得扔。”我捡起锥子,看见铁砧上,落了一片梧桐叶。傍晚,女儿发来一张照片,她挽着一个男人的手,笑靥如花。男人脚上的皮鞋,鞋跟锃亮,看不出半点修补的痕迹。我关了铺子的门,把那把旧锥子,收进了木箱底。
我父母都八十多岁了,我也五十多岁,现在我都不愿意去看他们,原因是什么呢那天
【13评论】【9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