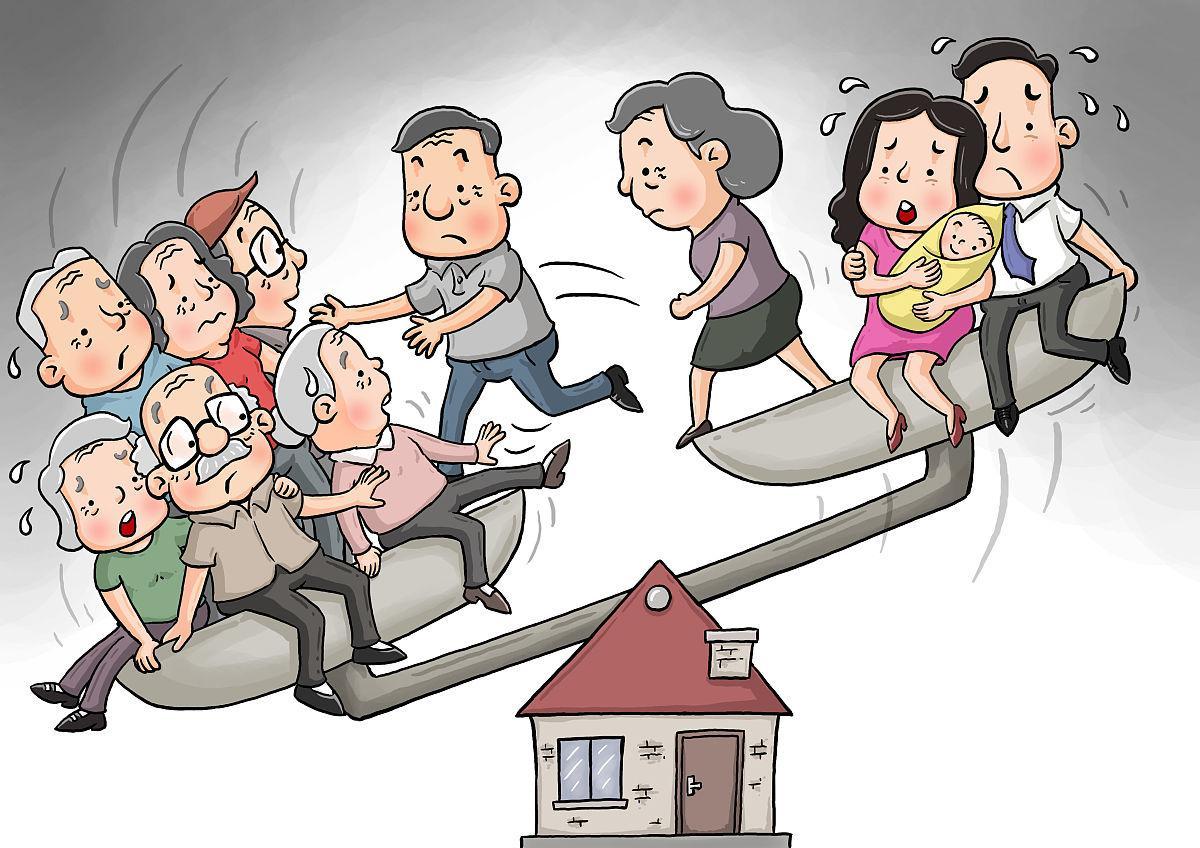一个18岁的姑娘,眼看追兵一脚踹开了家门,她一咬牙,跳上炕,挨着那个满头是血、昏迷不醒的陌生男人坐下。她冲着那帮凶神恶煞的兵喊:“别过来!他是我男人,得了传染病,头都烂了!” 1940年冬,华北大地正深陷日军“扫荡”的阴霾,河北平山县作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军民正与侵略者展开殊死周旋。 这一年的冬夜,18岁的农家少女姜达泉,用一场以清白和全家性命为赌注的豪赌,救下了一位身负重伤的八路军指挥员,这段生死情谊此后跨越四十三年,成为抗战时期军民鱼水情的生动注脚。被救的指挥员,正是后来晋升为开国少将的罗厚福。 彼时,百团大战刚刚结束,日军随即展开大规模报复性“扫荡”,晋察冀根据地军民面临严峻考验。 寒风如刀的夜晚,姜家的大门突然被撞开,一个满头是血的身影踉跄闯入。来人正是罗厚福,当时他作为八路军指挥员在战斗中头部被炮弹破片击伤,皮肉被削去一块,鲜血糊住双眼,身后日军的狼狗声和摩托车轰鸣声步步紧逼。 姜达泉刚满18岁,还是未订婆家的黄花大闺女。看着眼前随时可能断气的八路军战士,她心中虽有恐惧,却清楚记得乡亲们的共识:八路军是打鬼子的队伍,绝不能让他们死在自家屋里。 罗厚福虚弱地想向後门挪动,不愿连累这户无辜人家。姜达泉却突然爆发出惊人的力气,一把将他拽住,迅速把他推到炕角,扯过破被子盖住他的下半身。 她急中生智,从灶膛里抓出一把锅底灰,混着罗厚福额头的血水,在他脸上胡乱涂抹。转眼间,英武的战士就变成了面目全非、散发着怪味的“病鬼”。 此时,追兵的皮靴声已踹开院门。姜达泉心一横,脱鞋上炕,紧紧挨着昏迷的罗厚福坐下,将少女最珍视的名节彻底抛在脑后。 日伪军冲进屋时,只见昏暗油灯下,一个年轻姑娘正守着半死不活的男人,神情悲切。领头的伪军皱着眉用枪管挑开被角,姜达泉立刻做出癫狂的姿态,将罗厚福血肉模糊、沾满黑灰的脑袋往伪军眼前凑。 她嘶吼着声称男人得了“烂头瘟”,浑身流脓,碰者必死,还编造村头人家因该病死绝的谎言。血腥味与草木灰的怪味混杂在一起,让本就忌惮传染病的伪军吓得连连后退。 伪军骂了句“晦气”,捂着鼻子匆匆撤离。直到院子里的脚步声彻底消失,姜达泉才像抽干了力气般瘫软在炕,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 她颤抖着端来温水,一点点擦去罗厚福脸上的血污。接下来的三天,姜达泉白天紧锁大门,夜晚才敢熬米汤喂他,怕他乱动崩开伤口,就握着他的手轻声哼着家乡小调安抚。 这三天的朝夕相处,成为罗厚福此后半生最刻骨铭心的记忆。伤势稍稳后,罗厚福执意离开,他知道自己多留一刻,姜家就多一分灭顶之灾。 黎明时分,罗厚福在村口向姜达泉和她的父母深深鞠躬,许下报恩的承诺后,转身消失在晨雾中。这一别,便是四十三年。 归队后的罗厚福在战场上愈发勇猛,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历任旅长、军分区司令员等职,长期坚守鄂豫皖等地区的游击战争,立下赫赫战功。 1955年,罗厚福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中央军委补授军衔,他晋升为少将,成为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开国将军。 功成名就的罗厚福从未忘记那个平山县的少女,他无数次托人前往河北打听姜达泉的下落,却因当年撤离匆忙记不清确切村名,屡屡失望。 有人劝他放弃,说兵荒马乱的年代,人或许早已不在,但罗厚福始终坚定:“她是为了救我才冒的险,活要见人,死要见坟,找不到她我死不瞑目。” 岁月流转,青丝熬成白发,1983年,已是古稀之年的罗厚福终于得到确切消息:姜达泉还活着,就在平山县老家。 这位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老将军,激动得手抖得拿不住茶杯。当军车开进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小山村,罗厚福一眼就从人群中认出了那个身影。 当年俏丽的少女,已变成满头银霜、腰背佝偻的农家老太。两人相拥而泣的场景,让在场的警卫员和乡亲们无不潸然泪下。 罗厚福提出接姜达泉去城里享福,却被老人婉拒。她坦言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只要知道恩人活着,这辈子就知足了。 此后,罗厚福便以亲兄妹之礼相待,定期寄钱寄物,书信往来不断,这份用生命结下的情义,直至两人生命尽头都未曾褪色。 信息来源: 孝感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官方网站(孝德网):《孝感地方志人物传之八十五:罗厚福》 石家庄新闻网:《浴血沙场 誓死捍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