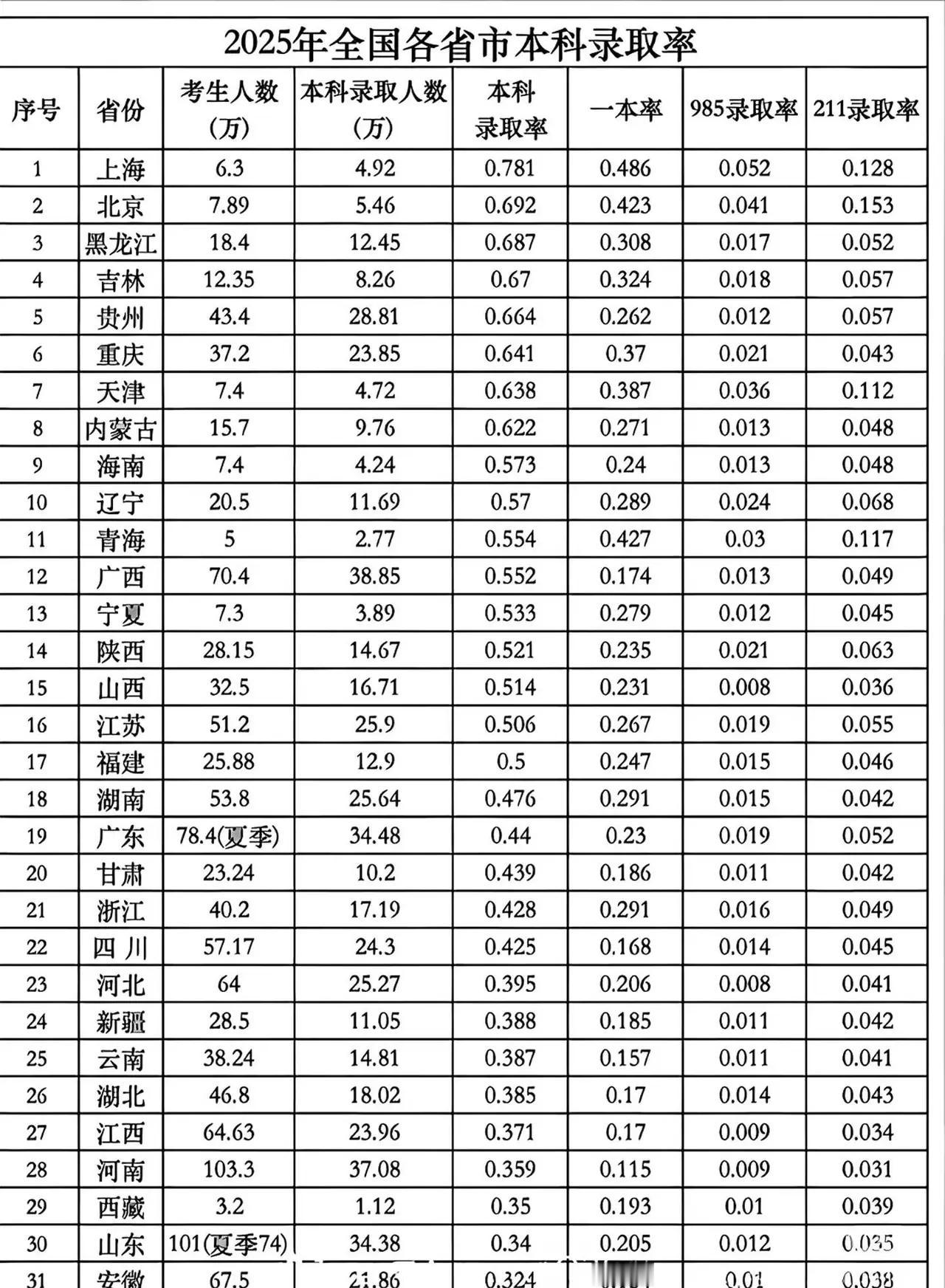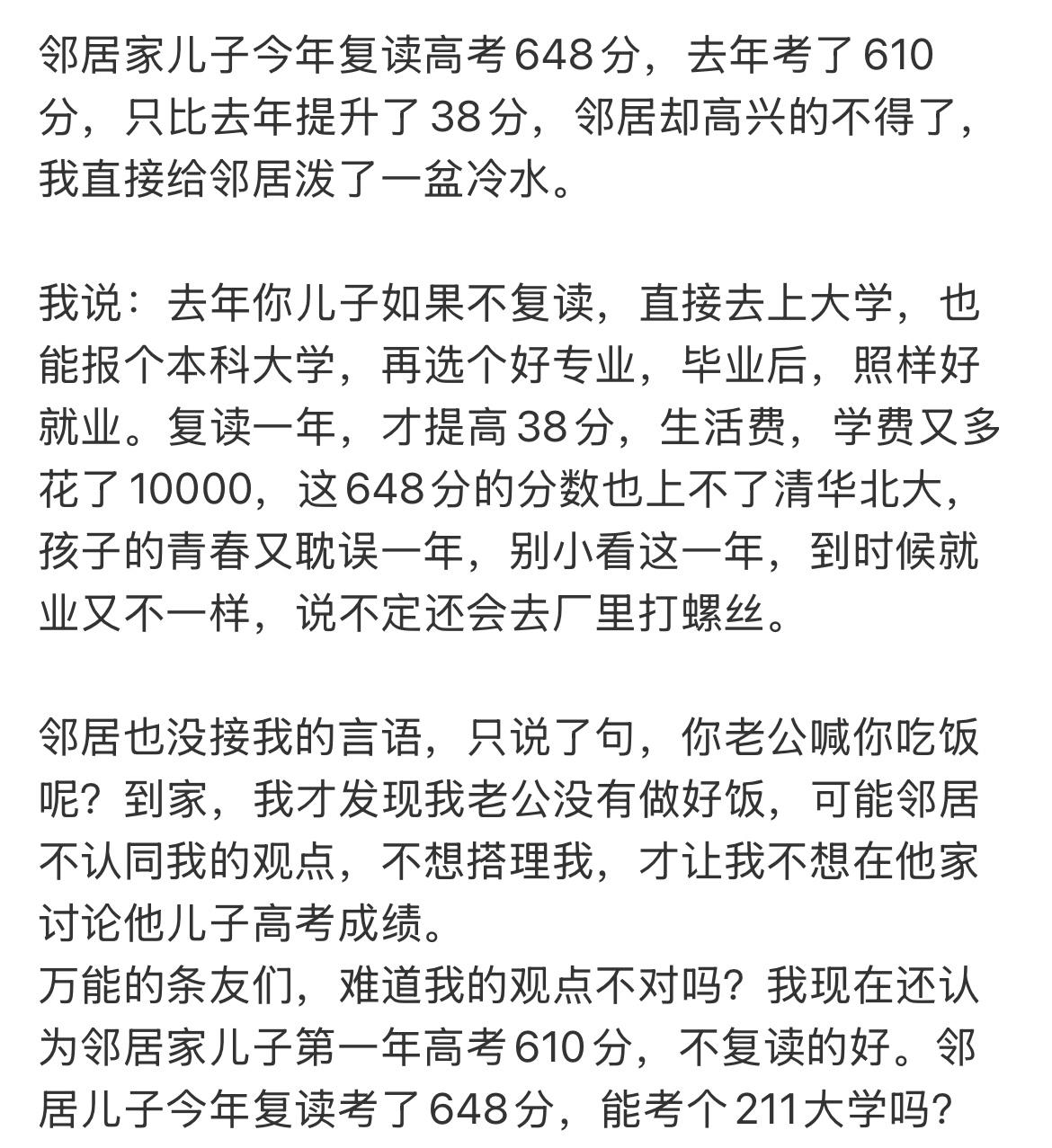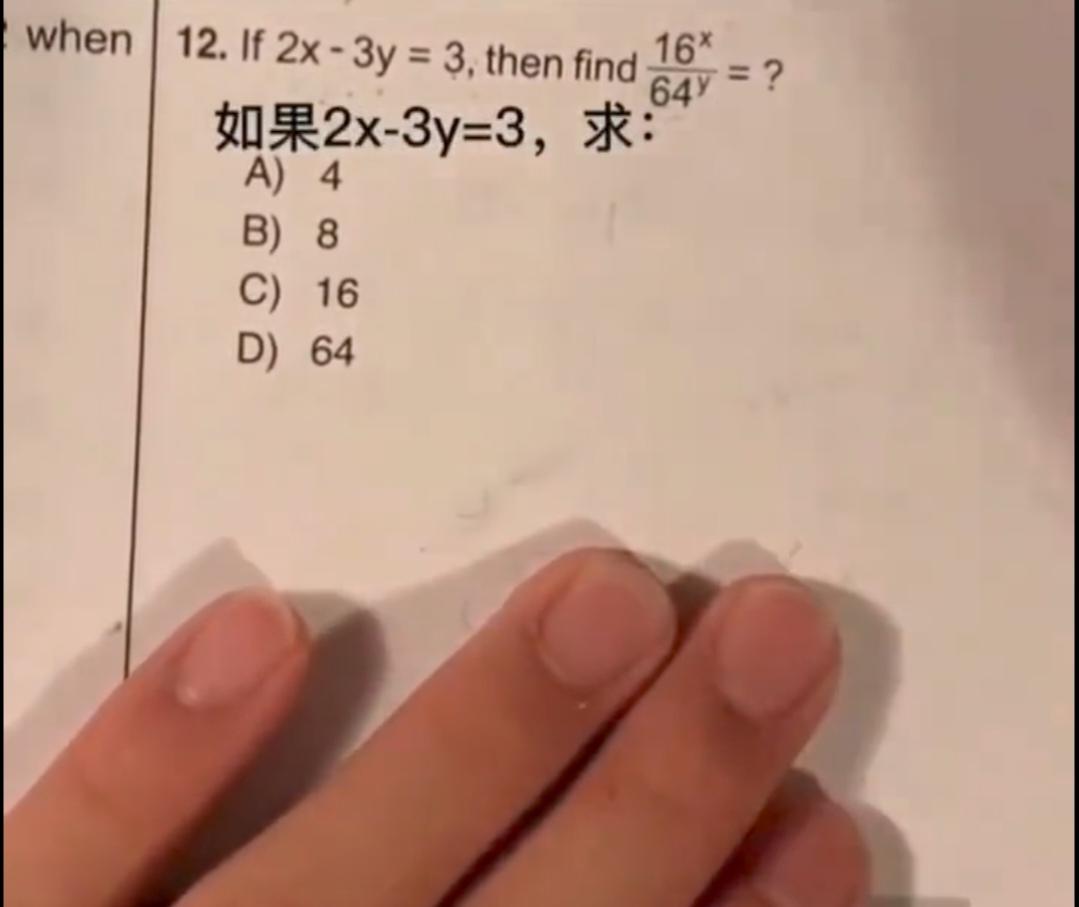1985年高考,我以几分之差落榜,回到学校复读。 正当我把课本翻得卷了边,父亲却在晚饭时放下筷子:“镇上老木匠要收徒,管吃管住,学满三年给工具。”他手指摩挲着碗沿,粗粝的茧子刮得瓷碗“沙沙”响,“你三叔说,木匠是手艺活,饿不死。复读……家里粮仓见底了。”我没抬头,扒拉着碗里的红薯干,听见灶台上的铁锅“咕咚”一声,像是谁把心事沉了底。 第二天我背着铺盖去了木匠铺。老木匠姓周,脊梁像弯了的秤杆,手里的刨子推得飞快,木花卷着香飘出来,在晨光里闪着金。“先学磨刨刀。”他扔给我块油石,“刀要利,心要静,不然木头会‘咬’手。”我蹲在门口磨了三天,刀刃映出脸时,手心已经起了层厚茧,碰水就疼。 第一次独立做板凳,榫卯总对不齐,周师傅拿过凿子在我手背上敲了下:“眼要准,力要匀,就像做人,不能偷工减料。”他教我认木纹,说松木软适合做床,榆木硬能打桌椅,“木头有脾气,你得顺着它,日子才稳当。”那年冬天特别冷,我和师傅守着炭盆赶工,给邻村王婶做嫁妆柜,雕花时手冻得发僵,师傅就把我的手按在炭盆边,“暖和了再刻,活儿糙了,人家姑娘要委屈一辈子。” 开春时,我终于做成了第一张像样的书桌。师傅摸着桌面的光纹笑:“能出师了。”我扛着工具回村,父亲摸着书桌的边角,指腹在木纹里蹭了又蹭,“比城里买的还光溜。”没多久,村里盖新房的都来找我打家具,李家娶媳妇要雕花木床,张家盖粮仓要结实的梁木,我每天天不亮就开工,刨子声、凿子声在村里响成一片。 有天去镇上买木料,撞见当年复读的同学。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胸前别着钢笔,说是在县中学当老师。“听说你成木匠了?”他笑着拍我肩膀,我手上的木刺扎了他一下,他也没躲,“挺好,咱们村以前打家具都得去县城,现在有你在,方便多了。”阳光照在他眼镜片上,反光里,我看见自己满手的老茧,忽然想起周师傅的话:“手艺在身,走到哪儿都能扎根。” 后来我在镇上开了木匠铺,招牌上写着“实在木作”。前阵子给小学做课桌椅,看见孩子们趴在崭新的木桌上写字,铅笔划过桌面的声音,像极了当年周师傅教我磨刨刀时,油石摩擦刀刃的轻响。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仰着脸问:“叔叔,这桌子能用多久呀?”我摸着桌面的木纹笑:“只要你好好爱护,它能陪你考上大学呢。” 前几天整理工具盒,翻出块磨得发亮的油石,旁边压着张泛黄的高考准考证。窗外的老槐树又开花了,我忽然想起1985年的冬天,周师傅把我的手按在炭盆边说的话。他没读过多少书,也不知道大学是什么样,但他一定知道,有些路看着弯,走下去却能踩出实诚的脚印。只是不知道,当年那些复读的同学,如今站在各自的讲台上、田埂上,是否也会想起那个落榜的夏天,我们曾一起望着同一片云,后来却在不同的地方,把日子打磨得发亮。
1985年高考,我以几分之差落榜,回到学校复读。 正当我把课本翻得卷了边,父亲
小杰水滴
2026-01-07 18:30:23
0
阅读: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