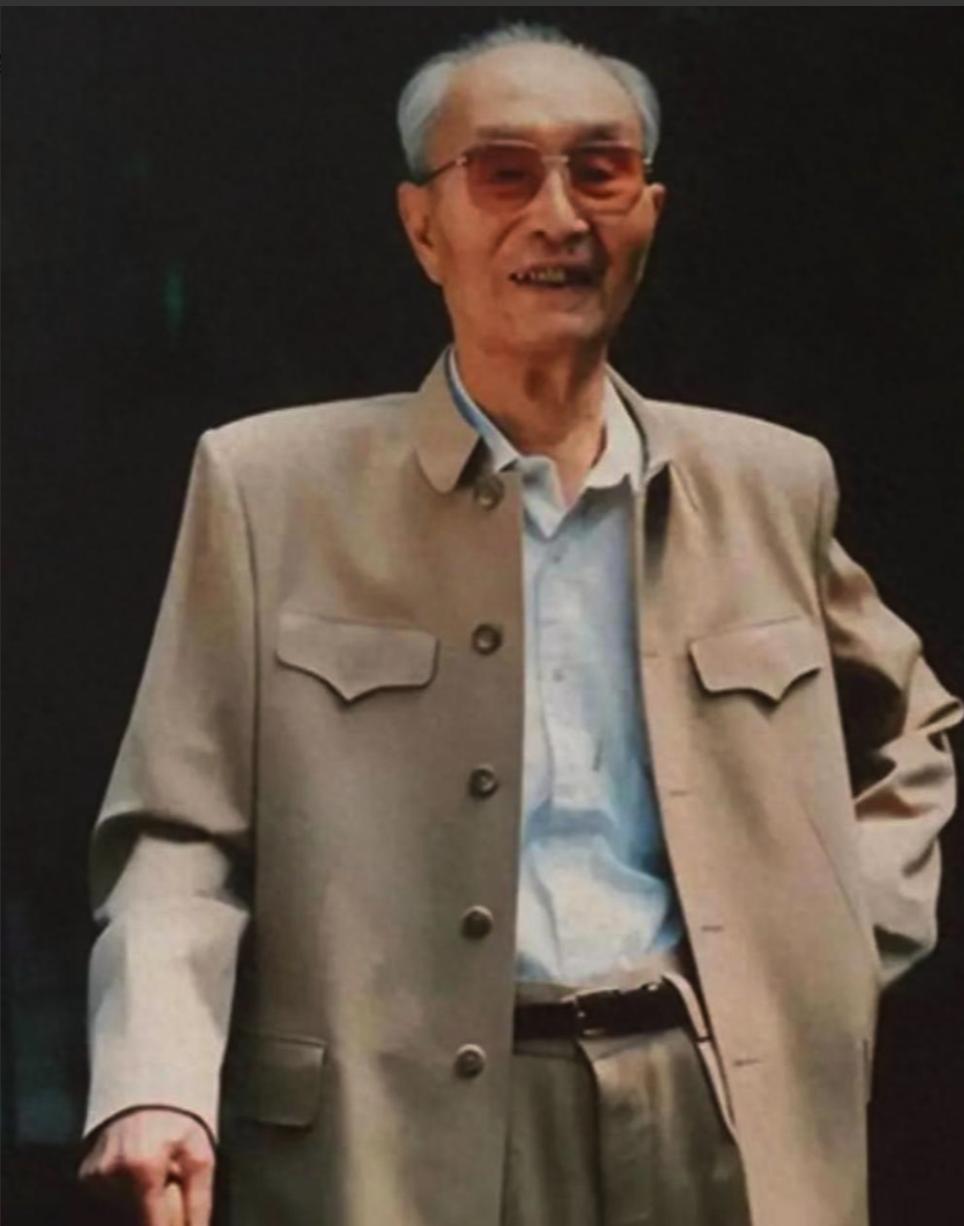1949年11月,上海街头,杨振寰等三名旧时代“讼棍”被戴纸帽示众。他们身着长衫,神情平静,却以代写诉状为名欺诈百姓,从公道维护者沦为鱼肉乡里的吸血鬼,遭人痛恨。 杨振寰三人不是科班出身的律师,连正经的法律典籍都没啃透几本,却在旧上海的城隍庙附近盘踞了十几年。 那时候的百姓大多不识字,遇到邻里纠纷、地主压迫、债务纠葛,想打官司却连诉状怎么写都不知道。杨振寰就是瞅准了这个空子,支起一张小木桌,摆上笔墨纸砚,再挂一块写着“代写诉状 包赢官司”的木牌,就敢堂而皇之地招揽生意。 他们嘴里说着“为民伸冤”,心里打的全是坑蒙拐骗的主意。来找他们写诉状的人,多半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穷苦人,有的攥着皱巴巴的几吊钱,有的拎着自家种的几斤大米,这就是他们的“律师费”。 杨振寰接过钱物,提笔就写,却从不会如实记录百姓的诉求,反而故意在字里行间埋下伏笔,要么夸大其词激化矛盾,要么偷换概念模糊重点,目的就是让官司久拖不决。 官司拖得越久,他们捞的好处就越多。原告急着要结果,他们就趁机索要“疏通费”,说要打点衙门里的人;被告怕输官司,他们也能暗中牵线,两头收钱。 要是官司侥幸赢了,他们会大张旗鼓地找上门,要求分走一半的赔偿款,说这是“辛苦费”;要是输了,他们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怪百姓命不好,怪官府太黑暗,自己则拍拍屁股走人,留下百姓哭诉无门。 有个苏北来的农民,因为田地被地主强占,千里迢迢跑到上海找他们写诉状,把身上仅有的十块大洋都给了杨振寰。结果诉状递上去石沉大海,农民再去找他理论,反被他指使地痞流氓打了一顿,最后只能流落街头,连回乡的路费都没了。这样的事情,在杨振寰十几年的“讼棍生涯”里,算不得稀罕事。 旧上海的司法体系本就腐朽不堪,衙门里的官员大多贪赃枉法,给钱办事是潜规则。杨振寰就是靠着钻这种制度的空子,和一些底层官员沆瀣一气,才得以横行霸道。他们不需要懂法律,只需要懂人心,懂怎么拿捏穷苦百姓的软肋,懂怎么在黑白两道之间周旋。 那时候的百姓,把他们当成救命稻草,却不知道自己握住的,是一根会吸光自己血汗的毒藤。他们穿着体面的长衫,说着文绉绉的话语,看起来斯斯文文,背地里做的全是伤天害理的勾当,硬生生把“代写诉状”这个本该帮人维权的行当,变成了欺压百姓的工具。 1949年上海解放后,新的政权带来了新的气象,司法系统开始肃清贪腐,倡导公正为民。政府不仅设立了免费的法律援助点,还组织识字班,教百姓认字,普及法律知识。 那些被欺压的百姓终于有了说理的地方,不用再求着杨振寰这样的讼棍,也不用再担心被坑骗。 杨振寰他们的生意一落千丈,可他们依旧不死心,还想着用老办法糊弄人,直到有几个曾经被他们坑害的百姓联名举报,把他们的所作所为一一揭发,新政府才出手将他们捉拿归案。 示众那天,上海街头挤满了人,有曾经被他们坑过的受害者,也有看热闹的路人。有人朝他们扔烂菜叶,有人大声唾骂,诉说自己的遭遇。 杨振寰三人低着头,脸上看不出丝毫愧疚,或许在他们眼里,自己只是“时运不济”,却没想过那些被他们害得家破人亡的百姓,承受了怎样的痛苦。他们的平静,不是坦然,而是麻木,是被贪婪腐蚀殆尽后的无动于衷。 杨振寰等人的落网,不仅是对几个不法讼棍的惩治,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旧时代的司法漏洞,滋生了太多像他们这样的蛀虫,而新社会的到来,斩断了这些蛀虫赖以生存的根基。 公道从来不是靠耍嘴皮子、玩心眼换来的,而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制度之上,建立在为民服务的初心之上。那些试图践踏公道、欺压百姓的人,终究逃不过历史的审判。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