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任副团长时,多年未见的老营长打电话过来,他在电话里说想过来看看,当年他转业时曾经承诺过等我啥时候调副团了就啥时候过来。如今我的目标实现了,他也该兑现自己的承诺。 老营长是坐早班火车来的。站台上,他头发白了大半,可腰板笔直,握手时力道大得吓人。我身后跟着几个营里的年轻干部,他挨个拍肩膀,拍得小伙子们龇牙咧嘴。办公室里风扇吱呀呀转着,他端起我的搪瓷缸子就喝,说还是这股子茉莉花茶味儿。 我本安排他住团招待所,他摆摆手:“就住营里,以前我那间宿舍还在不?”那间宿舍早改成器材室了,我劝他,他眼一瞪:“打地铺也行。”最后只好在值班室给他支了张行军床。晚上查岗,我看见他屋里灯还亮着,凑近一看,他正戴着老花镜,慢慢翻着营里的训练日志。 第二天一大早,起床号还没响,他就穿戴整齐站在操场边了。战士们跑操经过,他冷不丁吼了一嗓子:“第三列!步子压住!”几个新兵一激灵,队伍瞬间齐整了。吃早饭时,他端着餐盘坐到新兵中间,教他们怎么把馒头掰开夹腐乳。有个小战士筷子掉了,他顺手把自己那双递过去。 下午我开会,手机亮了一下,是营长发来的照片:老营长蹲在单杠边上,正给一个手上磨破皮的兵缠绷带。夕阳照在他灰白的鬓角上,柔柔的。 晚上说好给他饯行,食堂加了两个菜。他却不怎么动筷子,光看着战士们吃饭。忽然说:“我那会儿,最怕你们吃不好。”饭堂里一下子静了。一个二期士官站起来,端着汤碗:“老营长,以汤代酒,敬您!”呼啦啦站起来一大片。 第三天清早,值班员跑来说,老营长不见了。行军床收拾得干干净净,被子叠成标准的豆腐块。枕头下压着一张纸条和一卷用橡皮筋捆好的钱。纸条上就一句话:“伙食费。别来找,我坐最早班车走了。” 我追到大门岗。哨兵说,天没亮他就步行出去了,不让叫车。路尽头空荡荡的,只有初秋的风卷着几片黄叶,打着旋儿。
在我任副团长时,多年未见的老营长打电话过来,他在电话里说想过来看看,当年他转业时
嘉虹星星
2026-01-26 14:12:24
0
阅读: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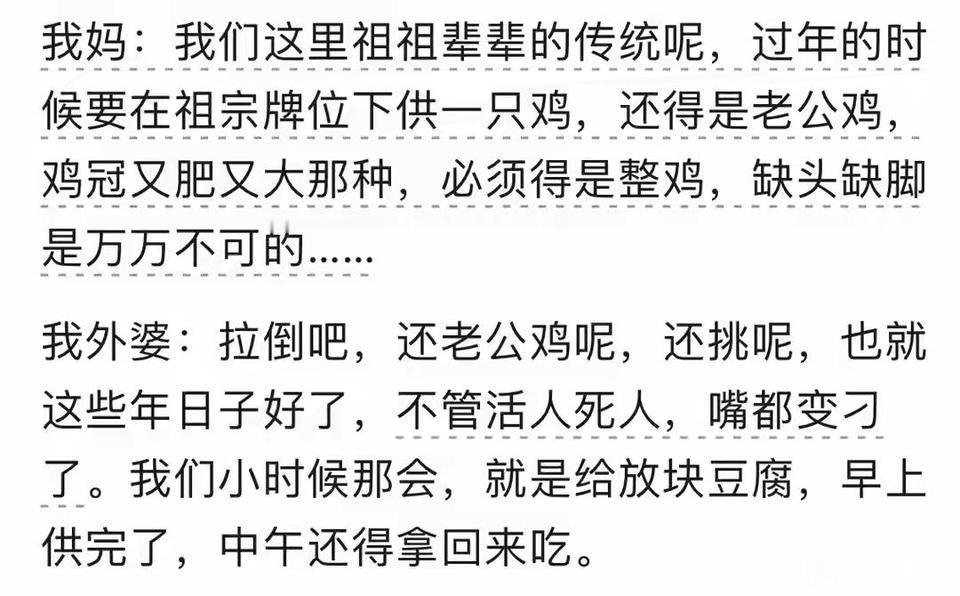



![[微笑]心疼!孙颖莎归国高烧落泪,大头贴身守护国乒全员暖心](http://image.uczzd.cn/2994916003774520217.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