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市场中,无数企业怀揣着逐利的梦想涉足其中,试图通过资本运作实现财富的快速增长。但是,金融市场就像一片深海,稍有不慎便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高盛反买,别墅靠海”这句略带调侃的网络流行语,背后却折射出金融大鳄在市场博弈中令人胆寒的影响力。中航油事件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惨痛案例,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设在新加坡的全资子公司——中航油,在看似风光无限的资本运作背后,因陷入高盛设下的圈套,最终吞下巨亏5.5亿美元的苦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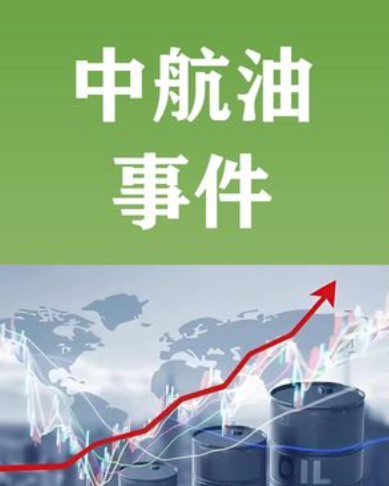
这一事件不仅深刻影响了中航油自身的命运,也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交易敲响了沉重的警钟,同时还暴露出国际金融资本背后的复杂博弈与残酷真相。

中航油成立之初,经营状况并不理想,连年亏损。直至航油集团派遣陈九霖前往新加坡掌舵,中航油才迎来命运的转折。陈九霖凭借出色的经营能力,带领企业实现扭亏为盈,并在2001年成功于新加坡上市,开启了中航油的辉煌篇章。其主营业务聚焦于从国外进口航油,凭借石油贸易庞大的规模,在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2003年,经监管部门批准,中航油获得在境外参与的资格。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监管的初衷是让中航油通过套保业务规避价格波动风险,保障企业主营业务的稳定运营。但中航油却擅自将业务拓展至新加坡的期权投机领域,这一违规操作无疑为后续的灾难埋下了隐患。

同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在战争阴云笼罩下,中东作为全球石油的核心产区,局势动荡不安。按照常理和历史经验,众多分析师纷纷预测,战争将导致石油减产,进而引发油价井喷式上涨。但是,美国能源部的意外之举打破了市场的预期,突然向市场抛售3000万桶石油储备,使得国际油价不仅没有上涨,反而狂跌至三个月低点,众多押注油价上涨的石油多头损失惨重。
此时的陈九霖却从中嗅到了“机会”,他果断在新加坡纸货市场大笔买入看涨期权,同时卖出看跌期权。新加坡纸货市场是一个纯粹的衍生品场外市场,这里汇聚了高盛、三井住友、巴克莱等国际资本大鳄。该市场的特殊之处在于合约到期后无需实物交割,仅通过现金结算,这也为后续的风险失控埋下伏笔。

幸运的是,油价在短暂下跌后快速反弹,中航油的第一笔期权交易便斩获数百万美元的收益。期权交易快速获利的特性,让陈九霖尝到了甜头,从此深陷其中,一发不可收拾。

2004年一季度,国际油价波动上涨,迅速逼近35美元一桶的历史高点。基于伊拉克战局逐渐平稳,石油出口恢复到战前水平的判断,陈九霖认为油价未来上涨空间有限,于是中航油在纸货市场反手做空,大笔卖出看涨期权,而其交易对手正是大名鼎鼎的高盛。
影响油价走势的因素错综复杂,涵盖供给、需求、库存、美元和战争等多个方面。在2004年一季度这个关键节点,虽然战争因素看似对油价不利,但其他四个因素却形成了强大的油价上涨驱动力。

从供给端来看,欧派克各成员国自2003年11月起每日减产90万桶石油;需求方面,2003-2004年,美国GDP季度增速一度超过8%,中国、印度等能源需求大国的经济增长同样强劲,对石油的需求持续高涨;库存层面,2004年初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原油库存处于历史低位,补库存需求迫切。
美元走势上,自2003年6月起,美元进入贬值周期,而美元与油价通常呈负相关关系,美元贬值进一步推动油价上涨。种种迹象表明,2004年正是历史上最大一轮油价牛市的起点,中航油在此时做空原油,已然踏上了一条注定悲惨的道路。
以中航油与高盛的看涨期权交易为例,若中航油以2美元的价格卖给高盛一个执行价为36美元的美式看涨期权,这意味着高盛支付2美元获得一项权利,可在合同期内,无论市场油价如何,随时以36美元的价格从中航油购买一桶原油。

当油价低于36美元时,高盛不会行权,中航油赚取2美元期权费;油价在36-38美元之间,高盛行权虽能在石油价格上获利,但扣除期权费后仍亏损,中航油盈利;一旦油价涨至38美元以上,高盛将获取巨额利润,而中航油的亏损则没有上限。这种收益有限、风险无限的交易,被巴菲特视为“定时炸弹”。
中航油之所以选择这种高风险操作,一方面是受到锚定效应的影响。在陈九霖的认知中,历史上油价从未超过35美元,他将油价上限锚定在这一水平附近,认为设置36美元的执行价并收取2美元期权费,只要油价不突破38美元便不会亏损,却未料到油价会不断刷新历史记录。
另一方面,期权交易能够美化财务报表。作为中资出海的龙头企业,中航油当时正谋划收购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为提升股价、吸引投资者,需要将财务报表做漂亮。期权费可直接计入收入,而期权产生的亏损在结算日前可置于表外,不影响报表利润,再加上纸货市场交易的隐蔽性,使得中航油的违规操作得以暂时掩盖。

2004年一季度,国际油价飙涨,中航油的仓位瞬间亏损580万美元。面对亏损,陈九霖最初打算平仓止损,但此时,中航油的两个外籍交易员以及外聘的咨询公司纷纷站出来,强烈建议不要平仓,而是向后移仓并放大空头仓位。
他们声称国际油价上涨不可持续,未来必将下跌,通过移仓可挽回损失,同时放大仓位既能增加未来盈利,又能获取更多期权费填补前期窟窿。但是,陈九霖并未察觉,咨询公司实为高盛的关联子公司,而那两名外籍交易员也早已与高盛勾结,这场导致中航油破产的期权交易正是咨询公司推荐的。
在咨询公司的蛊惑下,中航油与高盛等各大投行签署期权重组协议,不断后移仓位、放大空头头寸。2004年二季度,油价继续上涨,中航油账面亏损从580万美元激增至3000多万美元;三季度,中航油再次听从咨询公司建议,将期权交割日挪至2005-2006年,空头仓位放大至5200万桶。

与此同时,高盛等外资投行在中航油加仓后,大幅增加国际原油净多头持仓,推动油价持续走高。当油价突破50美元时,中航油亏损已达数亿美元。此前高盛和三井给予中航油的保证金优惠政策也突然反转,不仅要求补足保证金,还提高保证金比例,油价每上涨1美元,中航油就需补交5200万美元保证金。中航油为避免爆仓,不断注入资金,直至营运资金和银行贷款全部耗尽。

2004年10月9日,中航油流动性枯竭,陈九霖无奈向母公司汇报投机原油巨亏的情况。随后,航油集团为挽救局面,被迫卖出中航油15%的股票,筹集1.08亿美元注入中航油,但这仍无法填补巨大的资金缺口。
10月26日,日本三井率先发难,向中航油发出违约函并强行平仓,造成1.32亿美元实际亏损;11月8日,巴克莱资本和伦敦标准银行逼仓,中航油实际亏损飙升至3.81亿美元。10月29日,中航油在新加坡申请停牌;11月30日,中航油发布公告,宣布因无法注入保证金,终结衍生品交易,累计亏损高达5.5亿美元。

令人唏嘘的是,在中航油爆仓后的一个月内,油价大跌25%,这更凸显了此次事件背后的诡异与资本操纵的痕迹。
中航油事件给中国企业带来了诸多深刻警示。首先,企业在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时,必须严格遵守监管规定,明确业务边界,杜绝擅自扩大交易范围和风险敞口。其次,对市场形势的判断不能仅凭单一因素或历史经验,要全面、深入地分析各种影响因素,避免陷入认知误区。
再者,企业内部治理至关重要,应加强对关键岗位人员的监督和管理,防止内部人员与外部势力勾结损害企业利益。同时,面对国际金融大鳄的复杂手段和潜在陷阱,中国企业需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完善风险管理体系。

此外,此次事件也反映出国际金融市场的残酷与不公平,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自身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弱势地位,积极提升金融专业能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成为国际资本博弈的牺牲品。唯有如此,中国企业才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惊涛骇浪中稳健前行。
文字来源:春阳笔记的视频内容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