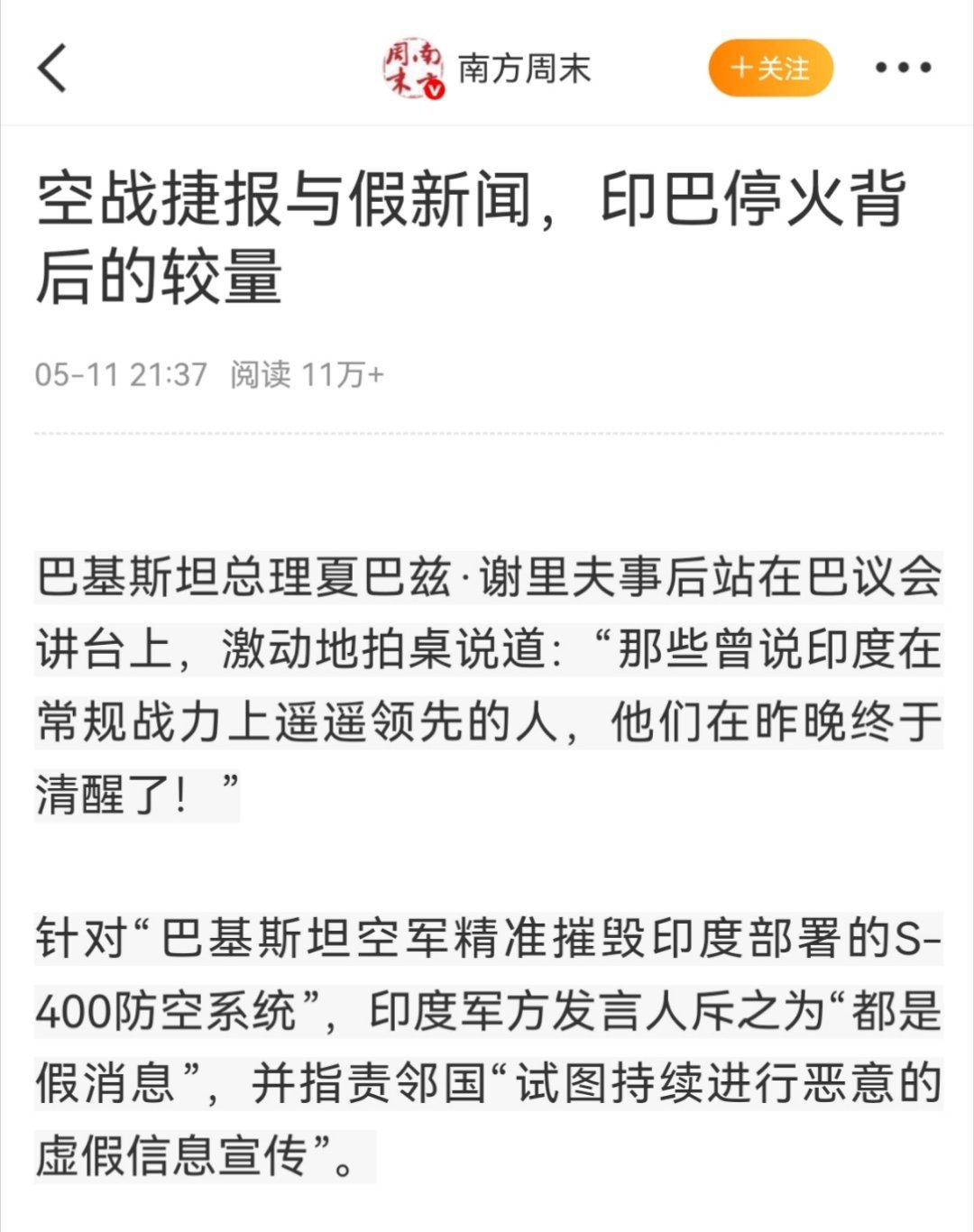1981年,梁晓声经人介绍与北京姑娘焦丹相亲,谁知一见面梁晓声就对焦丹说:“我每月工资42块5,要寄30块给东北老家。家里五个兄弟姐妹,大哥精神失常得吃药,我自己也因为长期熬夜写作,身体不是很好……” 1981年,三十二岁的梁晓声坐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单身宿舍里,看着桌角堆着的退稿信,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钢笔。 焦丹当时就愣住了。她刚在友谊商店试完新到的上海牌口红,挎包里还揣着《大众电影》编辑部的工作证——北京大妞见过最寒酸的相亲对象,也没开口就报家庭债务的。可眼前这东北汉子连茶缸都没准备,光端着搪瓷杯喝凉白开,袖口磨得发亮的蓝布衬衫倒是浆洗得挺括。 你猜怎么着?这姑娘第二天托介绍人捎话:"老梁实在,处着不累"。原来她爸是右派平反后塞进工厂当会计的,见多了满嘴跑火车的文化人。梁晓声把退稿信当草纸用的实诚劲儿,反倒让她想起牛棚里啃窝头的父亲——那年月说真话的比大熊猫还稀罕。 说实在的,梁晓声那会儿真没打算成家。宿舍墙上贴着《今夜有暴风雪》的手稿,纸边都卷了毛边。他白天在北影厂当文学策划,晚上趴在缝纫机改的写字台上改小说,烟灰缸是午餐肉罐头抠的,最奢侈的家具是花五块钱从信托商店扛回来的瘸腿藤椅。就这条件,媒人还劝他吹牛说"在文化部有关系",他当场把钢笔拍桌上:"我要会扯谎,早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改成样板戏了!" 焦丹头回来宿舍约会,梁晓声正在煤油炉上煮挂面。铝锅盖叮当响,他慌得用脚把床底的脏袜子往里踢。结果姑娘弯腰帮他拾掇起散落的稿纸,指着《雪城》里描写知青啃冻土豆的段落说:"这段得改,我插队时饿极了连桦树皮都嚼"。后来《年轮》里那个偷食堂馒头的女知青,原型就是蹲在煤炉边择菠菜的焦丹。 现在看这段姻缘像小说桥段,当年可是扎扎实实的烟火日子。梁晓声领结婚证那天,揣着刚发的稿费给媳妇买双尼龙袜,剩下的钱全换成粮票寄回黑龙江。洞房夜俩人在北影厂后墙根散步,焦丹突然说:"你那件蓝衬衫留着,等咱们孩子大了当传家宝"。三十年后梁晓声在《人世间》里写周秉昆和郑娟,笔尖还带着当年煤油炉的烟火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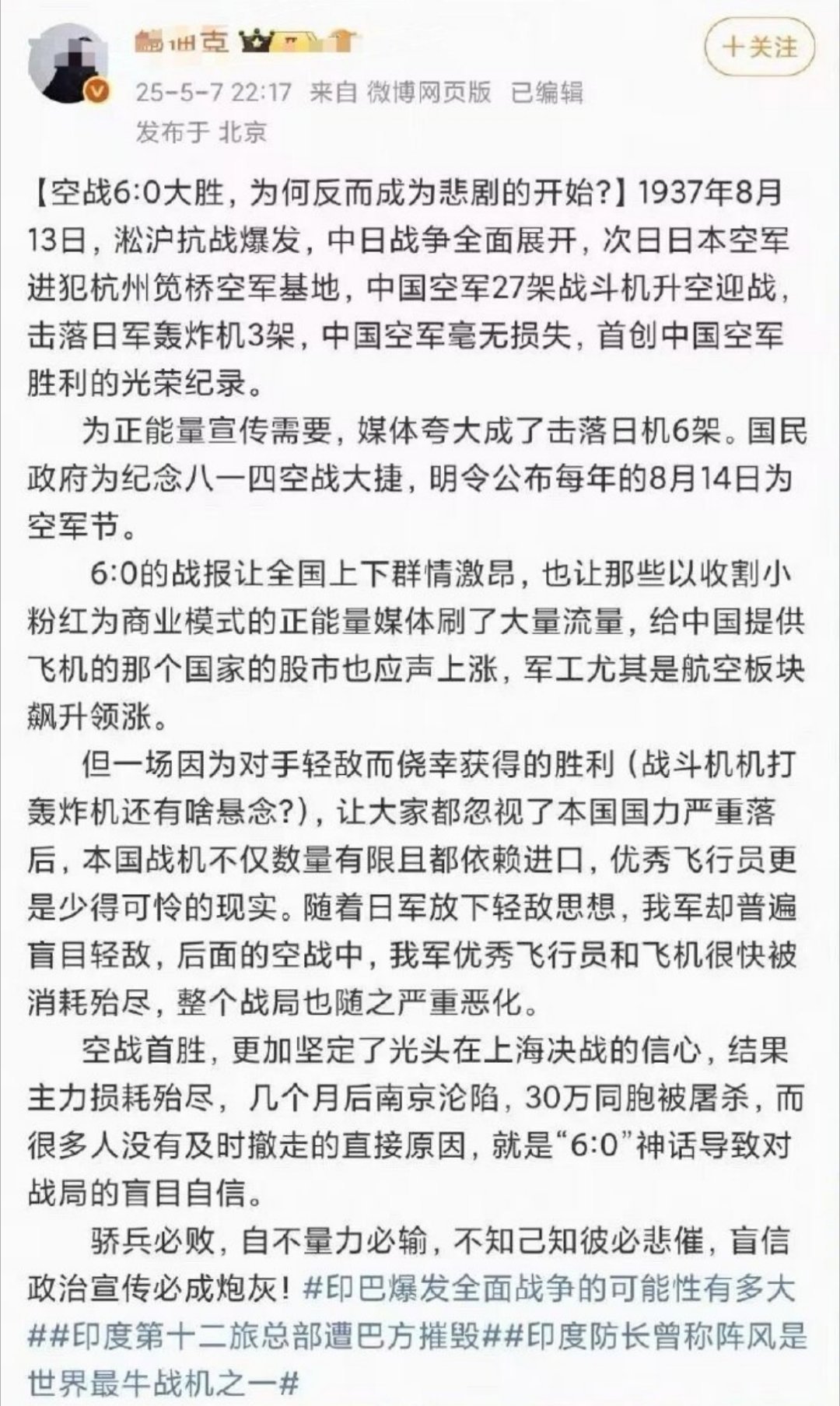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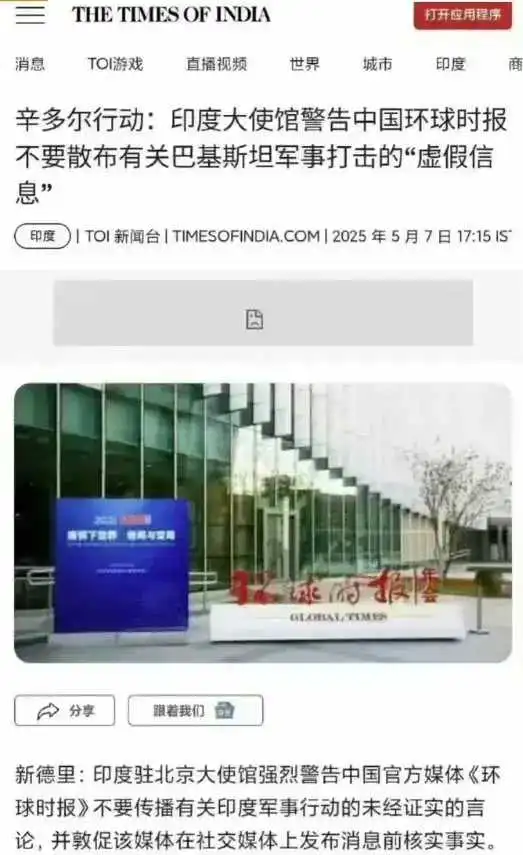
![该不该帮她做两杯呢?[惊恐]](http://image.uczzd.cn/3570558181354908261.jpg?id=0)
![表姐给我介绍奇怪的工作怎么拒绝?[汗]](http://image.uczzd.cn/5691864303793511222.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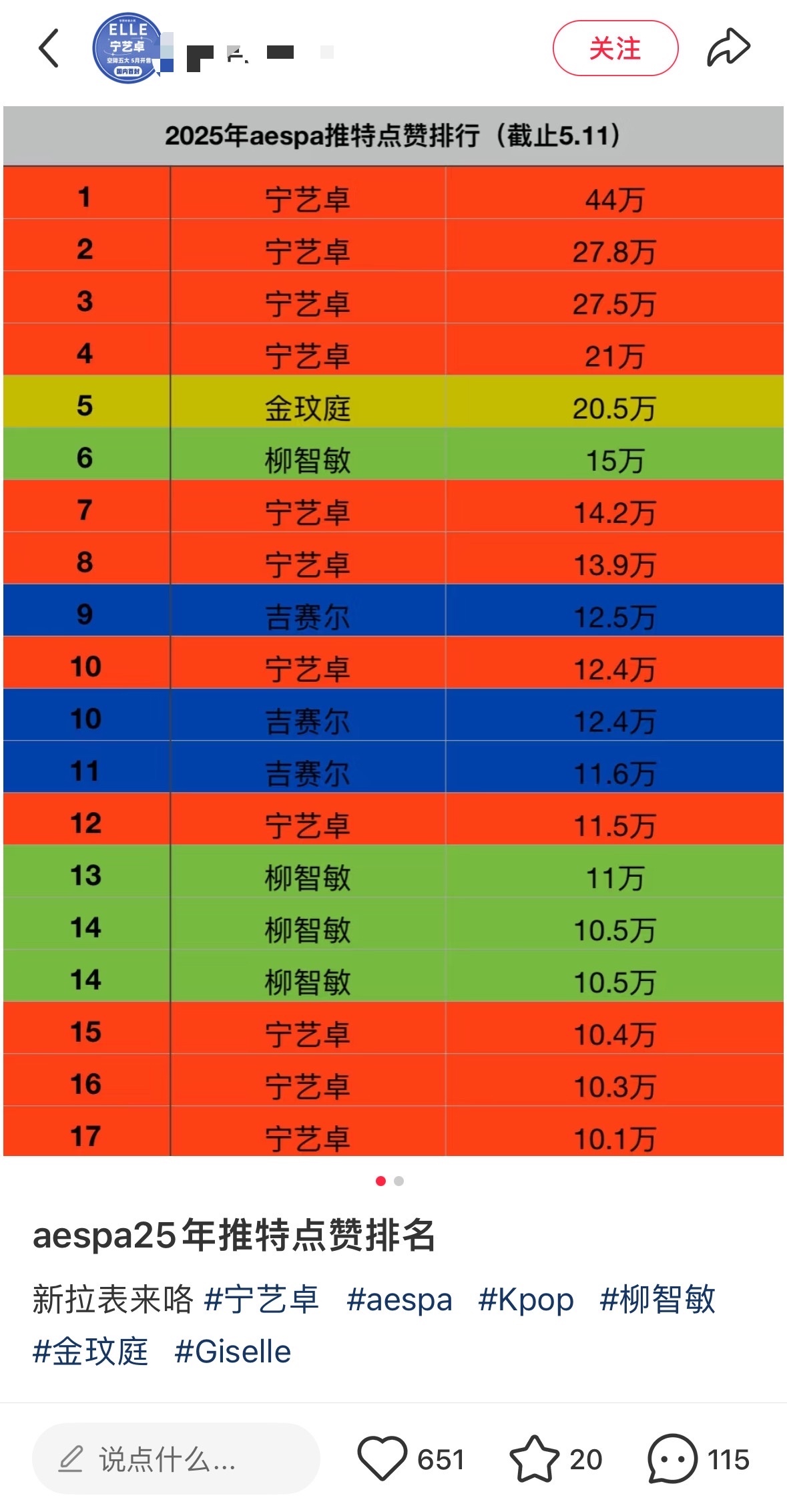
![唐L:糟糕,瞧不上我?[呲牙笑]这明显不是冲我来的了除了尺寸差不多,一点都不像](http://image.uczzd.cn/16574040333992958169.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