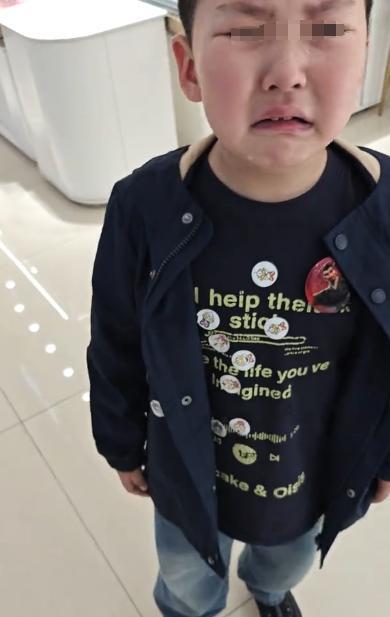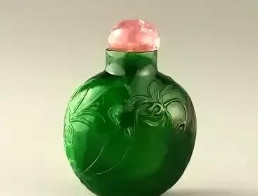2016年,山东潍坊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老汉,徒手建起了一座奇形怪状的“七层小楼”,只为等他的两个弟弟回家,可惜他并不知道,两个弟弟早已去世,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山东潍坊的郊外,有一座并不起眼的七层小楼,混杂在一条尘土飞扬的乡间土路旁,若是路过,初看之下,它更像是一堆尚未清理的建筑废料,斜斜歪歪地堆叠着,仿佛风一吹便会散去,但若你驻足细看,又会觉得这座楼带着某种奇异的吸引力——像是一位老者蹒跚着,却倔强地站在岁月的风口中,不肯倒下,游客好奇地举起手机记录它的模样,新闻记者曾三番五次前来探访它的来历,而本地人,尤其是年长一些的村民,在经过它时往往会收起笑容,低声说一句:“那是胡光州给弟弟们盖的家,” 胡光州,这个名字在胡家岭村并不陌生,几十年前,他是村里出了名的苦命人,父母早逝,兄妹人丁稀薄,留下三个年幼男孩相依为命,他是老大,从少年起便扛起了整个家庭的担子,那时的他正值青春年华,身板瘦削,却总背着个装满草药的竹筐翻山越岭,身后跟着两个鼻涕横流的小弟弟,那幅画面曾被村里人看作是乡间最动人的兄弟情。 生活艰难,却也有盼头,胡光州没能继续学业,把能找到的活都接了下来:修房顶、挑水泥、挖土方,他毫无怨言,一次为人修房不慎从高处跌下,头部撞在石头上,从此脑子里像是打了个结,说话有些混沌,逻辑也时常颠倒,亲近的人都知道,那次事故之后,他的精神出了些问题,但他依然记得两件事:弟弟们要读书,家里要盖房。 在他的照料下,两个弟弟顺利长大,读书不成,却也很快学了手艺,跟着包工头去了南方的建筑工地务工,临走那天,三兄弟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蹲了许久,胡光州把自己攒了半年、皱巴巴的零票子塞给弟弟们,嘴里还念叨着“等挣了钱,就回来盖房子”,那是他们共同的愿望——一栋宽敞明亮的大瓦房,让兄弟仨安安稳稳住在一起。 这份愿景还未实现,命运却急转直下,先是二弟在工地上被倒塌的钢筋砸中,当场身亡,还未从悲痛中走出,几个月后,三弟在返乡途中遭遇车祸,也撒手人寰,两个鲜活的年轻人,就这样先后成了冰冷的骨灰盒,被送回了村里。 那段日子,村里人常在祖坟地看见胡光州默默坐着,怀里抱着两个骨灰盒,一坐就是一整天,等到春天来临,他忽然开始在村口的一块荒地上忙碌起来,没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捡废砖、搬木板、收铁丝,甚至连别人拆下不要的破瓦片也不放过,有人以为他又犯病了,但很快发现,他每天蹲在地上和泥、垒砖,似乎是在建一座房子。 这不是普通的建房工程,没有图纸、没有帮手、没有机器,所有的材料都是他在村里四处搜集来的,他用铁丝代替钢筋,用废布封堵缝隙,用碎玻璃拼凑窗户,不管刮风下雨,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干着,村干部曾多次劝他停手,说这楼盖不牢,危险,他却固执地不肯放弃,口中喃喃重复着“弟弟回来没地儿住”。 三年时间,这栋奇形怪状的七层小楼竟然拔地而起,每层高度不足一人,整体如同蒸笼般层层叠加,墙体东一块西一块地糊着黄泥,顶上还插着一根歪斜的竹竿,楼内摆设极为简陋,地上摆着三个豁口的粗瓷碗,墙上贴满烟盒纸,有人说那是他给弟弟们“装点新房”的方式。 这座小楼很快引起了外界的关注,文化馆的专家看过后称其为“民间建筑奇观”,媒体记者接踵而至,拍照、采访、记录,甚至有人建议将其列为乡土文化遗产,可胡光州不关心这些,他每天依旧围着土楼转悠,掸灰、擦窗、修补残破的墙缝,仿佛在为即将归家的亲人做最后的准备。 政府为他在村里另盖了两间新房,配齐了家具,还安排了照料他的护工,但他依旧把更多时间花在那座歪楼里,村民晚上路过时,常能看见土楼窗口透出昏黄的烛光,有人说他在楼里烧纸,有人说他在摆饭,有人说他在和“弟弟们”聊天,每年过节,他都要在楼前点上三串鞭炮,摆上三碗热腾腾的饺子,那是弟弟们小时候最爱吃的。 有人觉得他疯了,也有人说他比谁都清醒,那座楼不是为了住,而是为了记,对胡光州来说,土楼不是奇观,是承诺,他用三年时间、一人之力,把一段无法言说的亲情铸进了泥土砖瓦之间,它摇摇欲坠,却承载着他全部的牵挂和回忆。 如今,土楼依旧立在村口,墙缝间钻出了野草,窗棂上挂着蜘蛛网,来观的人络绎不绝,有人感动落泪,有人拍照留念,而村里的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参观完后,总会低声议论:“那是哥哥给弟弟们盖的家,” 信息来源:潮新闻客户端——第一现场 山东“七层妖塔”建造者背后故事引热议 当地考虑其情感暂不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