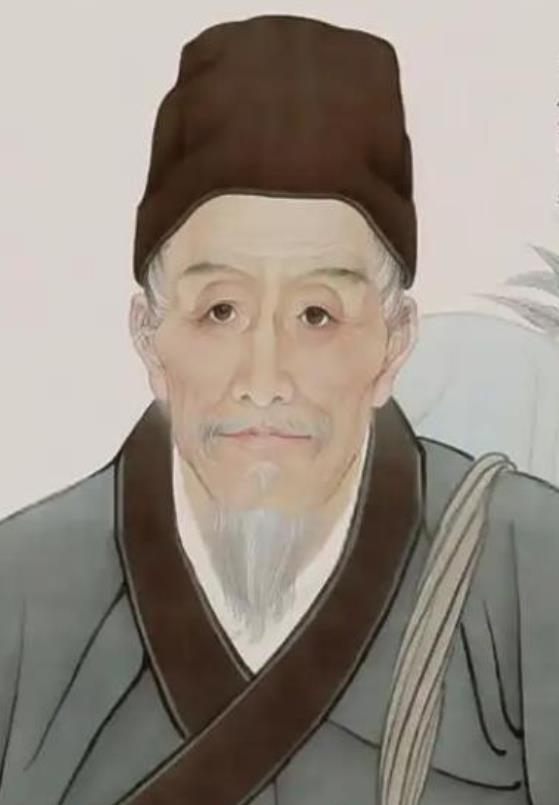李时珍外出就诊时,一个20岁的青年从人群中钻了进来,李时珍看了一眼就说:你只剩下3个时辰的寿命了,赶紧回家跟家人团聚吧。”小伙听到后破口大骂“我不过就是肚子痛,怎么就活不成?什么破郎中!”
明朝嘉靖年间的一个晌午,湖北蕲州城东的药铺外扬起一阵尘土,骡蹄声由远及近,二十出头的富家公子王守业捂着肚子冲进医馆,腰间玉佩叮当乱响。
只见他面色惨白如纸,嘴唇泛着乌紫色,额头的汗珠子顺着下巴颏往下淌,活像刚从蒸笼里捞出来。
坐堂大夫正是年过五旬的李时珍,他抬眼扫了扫来人,手指刚搭上脉门就皱起眉头。
脉象跳得又急又滑,像是有人拿着小鼓槌在皮肉底下敲快板,再细看年轻人青筋暴突的手背,指节已经泛起不祥的灰白色。
问诊得知,这位少爷中午在酒楼吃了两斤酱牛肉、十来个熏鸡腿,灌下半坛子烧刀子。
酒足饭饱后听说西山有野兔,竟跟着兄长骑马追猎,纵马跳过三尺高的土坡。
此刻他腹中绞痛如刀绞,每喘口气都像被人往肋条骨上踹一脚。
李时珍收回诊脉的手,默默合上檀木药箱。,望着疼得打摆子的年轻人,话在嘴里转了三圈才吐出来:"赶紧回家见亲人最后一面,还能赶上吃晚饭。"
此话一出,抓药的小伙计吓得打翻了甘草罐,看热闹的街坊把门框挤得吱呀响。
可王守业哪里受得了这个气?他瞪圆布满血丝的眼珠子,骂骂咧咧摔了诊台上的脉枕,临走还往门帘上啐了口带血的唾沫。
围观的百姓瞧得真切,那公子哥儿走路已经打晃,后脖颈的汗把绸缎衣裳浸出巴掌大的湿印子。
日头偏西时分,城西牌坊底下传来阵阵惊呼,人们围作一团指指点点,只见王守业蜷缩在青石板路上,嘴角挂着黑红色的血沫子,肚子鼓得像塞了三个西瓜。
几个胆大的凑近了看,发现他身下淌出黄褐色的污水,腥臭味熏得人直捂鼻子。
闻讯赶来的仵作验过尸首,说这人的肠子绞成了麻花,肚里灌满了粪水脓血。
有经验的郎中一看就明白,这是吃饱喝足后剧烈颠簸,把胀满的肠子甩脱了位置,就像装得太满的米袋子,经不住上下抛接,里头的米粒全搅成了糊糊。
要搁在现而今,这种急症送进医院就得开刀,大夫们会剖开肚皮,把打结的肠子捋顺了,再把腹腔冲洗干净。
可那是四百多年前的大明朝,莫说消毒止血的法子,就连能切开肚皮不让人疼死的麻沸散都失传多年了,任凭李时珍医术通神,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命消逝。
这事在蕲州城传得沸沸扬扬,有骂郎中心狠的,有说公子命薄的,倒是那些平日里胡吃海塞的纨绔子弟都收敛不少。
茶楼酒肆里添了桩新忌讳,谁要敢吃饱了蹦跶,准保被同伴拽着袖子提醒:"仔细肠子打结!"
后来李时珍在药典里记了一笔,说饱食后忌奔走跳跃,他用"谷满肠肥,动辄气逆"八个字,把血淋淋的教训化作治病良方。
有那读过书的明白人揣摩,老郎中当年当众判人生死,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与其让病家抱着虚妄希望受罪,不如把话说明白了好预备后事。
这事儿给后世提了个醒:人身上的零件儿金贵得很,经不起瞎折腾,就像老辈人常念叨的,吃饭七分饱,做事留三分,那些个拿身子骨不当回事的,往往等不到阎王索命,自己先给五脏庙点了把火。
要说他最难得的地方,倒不是他能断生死,而是敢说真话,那时候当郎中的讲究"宁开十副药,不吐半句丧",可他偏要把窗户纸捅破。
信息来源:张其成,《李时珍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