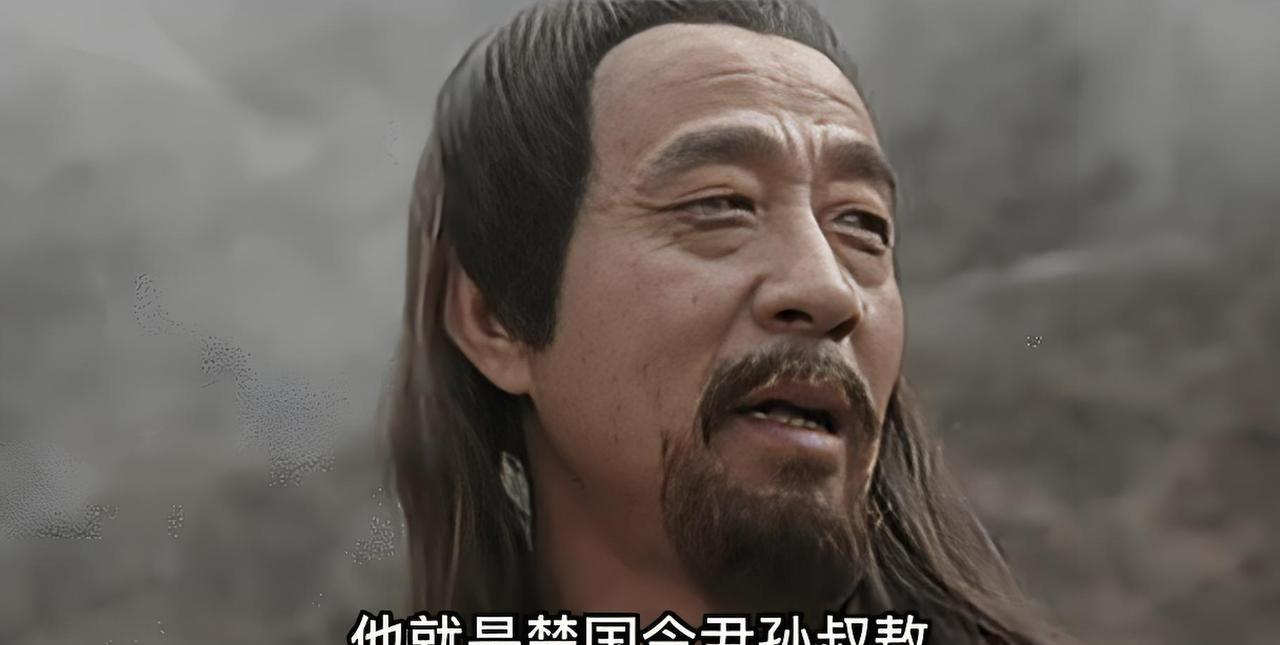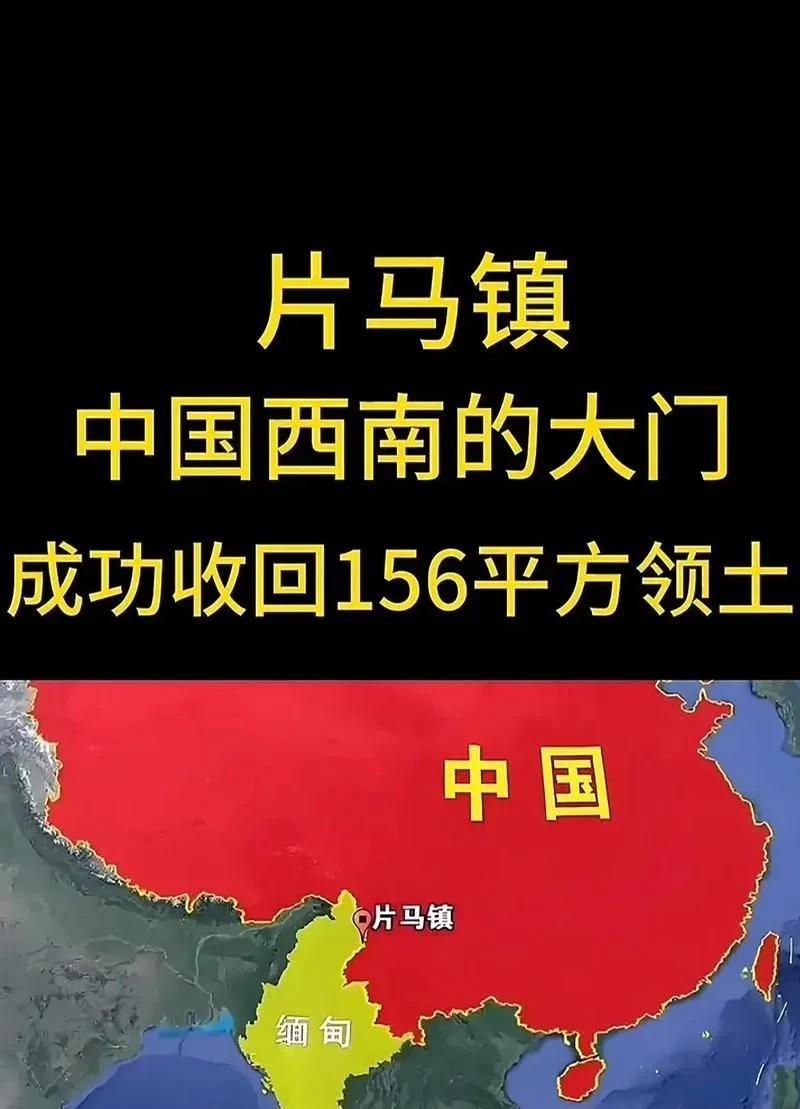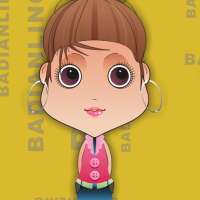1945年12月,戴笠首次踏足天津日租界的军统联络点,他盯着站内花名册许久,突然扭头对站长陈仙洲撂下硬邦邦的话:“余则成这年轻人,天津站怕是容不下他。” 1945年12月,天津清冷的风像刀子,吹在脸上生疼。 这天,戴笠到了天津。 他没大张旗鼓,也没有惊动地方警署,只是按军统内部惯例,悄无声息地视察。 他这个人,惯会突然造访,一声不吭就到门口。 军统天津站几位头面人物这几天早就绷着神经了。谁也说不准戴笠这趟是来安抚人心,还是要清算旧账。 站长吴敬中提前几日就开始准备材料,副站长陆桥山、行动组的马奎也没闲着。 人事复杂、派系分化,谁都怕站错了队。 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间节点——抗战刚结束,南京那边的局势翻江倒海,没人知道军统还能撑多久。 可谁也没想到,戴笠只见了两个人,一个是吴敬中,按规矩得见;另一个是余则成,一个在天津站内资历不深、但来头颇为特殊的小人物。 其他人等了一天,饭也没吃上,话也没听见,最终被通知“会见取消,戴处座已返北平”。 外人看这情形,摸不着头脑。 但懂内情的都明白,天津这一趟,戴笠不是来听汇报的。他是来试探,是来传递信号的。 而余则成,就像是他特意带到台前的一面镜子。 那时候的戴笠,表面看风光不减,其实早被架在火上。 他这几年的权势如日中天,军统系统庞大无比,遍布全国各地的站点、情报网密如蛛丝。 他手下人上百万,能调动的资源比一般军政高官还要多。 但问题也出在这儿,他的强大,已经让很多人不安。 “八人会议”刚刚在北平开完,会上的气氛相当不好看。明面上是研究警务整顿,实则是专门围绕如何削弱军统展开。 主持人宣铁吾,是陈诚的人,陈诚是蒋介石最倚重的军事亲信之一。 他和戴笠积怨已久,加上陈果夫、陈立夫那两位党务大佬,一起围堵军统,一点不留情面。 戴笠也不是没察觉。 他早知道“老蒋”忌惮军统权势过大,也知道三陈在背后递刀。 他在北方频频动作,打的就是一张“肃奸”牌,他说服蒋介石,把全国肃奸事务交给军统处理。 这张牌表面上是忠心,实际是“保命符”——一方面借肃奸来刷政绩,一方面借清查名义调整地方站点,清除异己。 于是北平、上海、天津这些重镇,成了他的主要战线。 王克敏、曹汝霖这些在汪伪时期名头响亮的汉奸,一个接一个落网,就是他那几个月抓的典型。 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是他试图重建蒋对他的信任,也是他想向党内其他派系释放一个信号:军统还有用,戴笠还没老。 问题是,这种效忠姿态并不见得能收效。 蒋介石此时考虑的,是整个国民党体制的重组,情报系统、特务系统、警务系统之间的权力再分配。 军统再强,也要被剪枝,何况他对戴笠早就有疑虑。 所以这次天津之行,更像是戴笠的“底线试水”,他已经不在乎流程、不在乎站内平衡,也不再理会那些按部就班的汇报。 他只想知道:这片摊子上还有没有他可以信的人。 余则成的出现,不是偶然。 他并不负责主要事务,也没有军统高层背景,但他是戴笠亲自安排进天津的。 是当年在重庆情报科被挑中,一路调任、培训、空降到天津,他的存在,就像是戴笠在这摊浑水里安的一只哨兵。 按说这种人在天津不该有太大话语权,但偏偏这一天,他成了唯一被戴笠“亲自约见”的非站长级成员。 两人谈了什么没人知道,传出去的消息也很模糊。 只知道戴笠离开前看了站里的花名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句:“余则成这年轻人,天津站怕是容不下他。” 这句话意味深长。 表面像是在为他叫屈,实际却像在为他点名。 “容不下”不等于“调走”,更像是告诉旁人:这人是我的,我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余则成什么也没说。 他向吴敬中点了头,规规矩矩地退了出去,他没有告谁的状,也没有递交密报。 他只是照着戴笠的习惯,说了几句场面话:“天津风平浪静,站里人心稳定,长官威信犹在。”这些话戴笠听惯了,但这时听来,比什么报告都顺耳。 戴笠不是不知道天津的问题,但他已经没有心力去一一整顿。 他取消了所有其他会见,一句“天津是不是在闹霍乱?”把所有人打发得干干净净。 马奎、陆桥山原地愣住,连材料都没递上,心里清楚:这一轮,他们被晾着了。 这就是军统的现实。不是你功劳大就能见老板,也不是你资历老就有话语权。你是哪一边的人,你能不能让戴笠“舒服”,这才是关键。 而戴笠此时,更需要的是“舒服”。 北平那边的会开得他心烦意乱,南京的局势每天都像上紧的发条。他本以为自己能撑过这波“肃奸维稳”,没想到老蒋的态度越来越冷淡。 军统几十年基业,眼看就要改旗易帜。 毛人凤的中统步步紧逼,警训系的人虎视眈眈。派系倾轧的刀口,就架在他的脖子上。 天津站这一趟,他本没指望解决问题。 他只是来确认底线,还能不能握住。 他没有批评谁,也没有清算谁,更没有“整风”。但他以最冷淡的方式,做了最清晰的划线。 后来余则成被调离天津,去了别的站点。 再后来戴笠去南京,准备飞往浙江,飞机在山中坠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