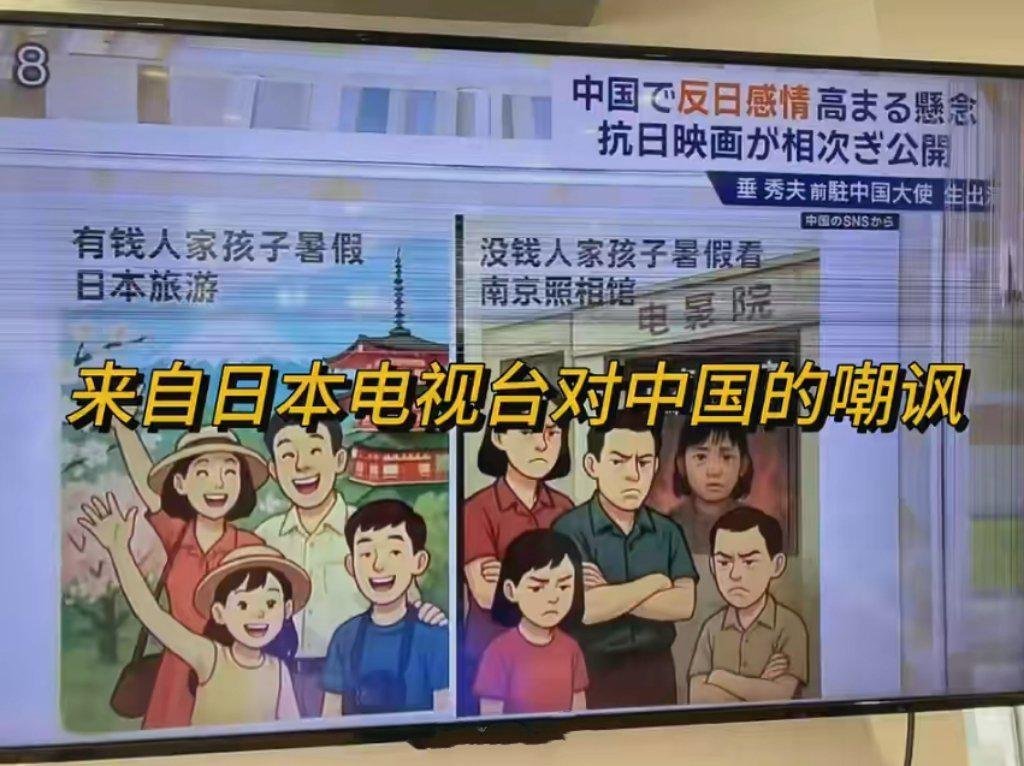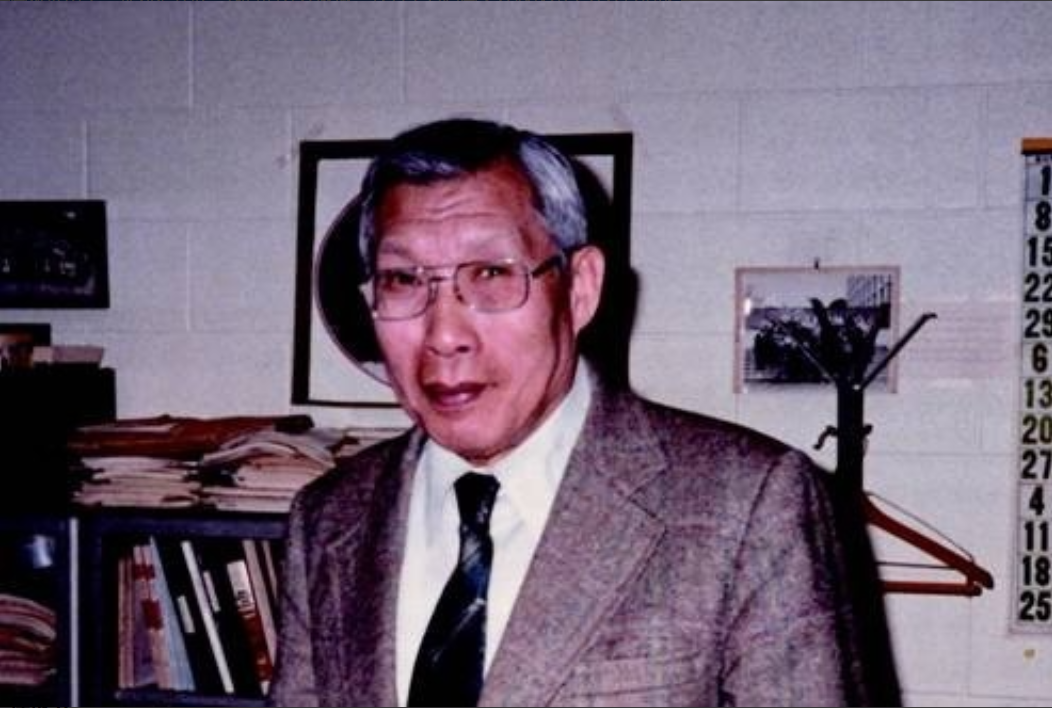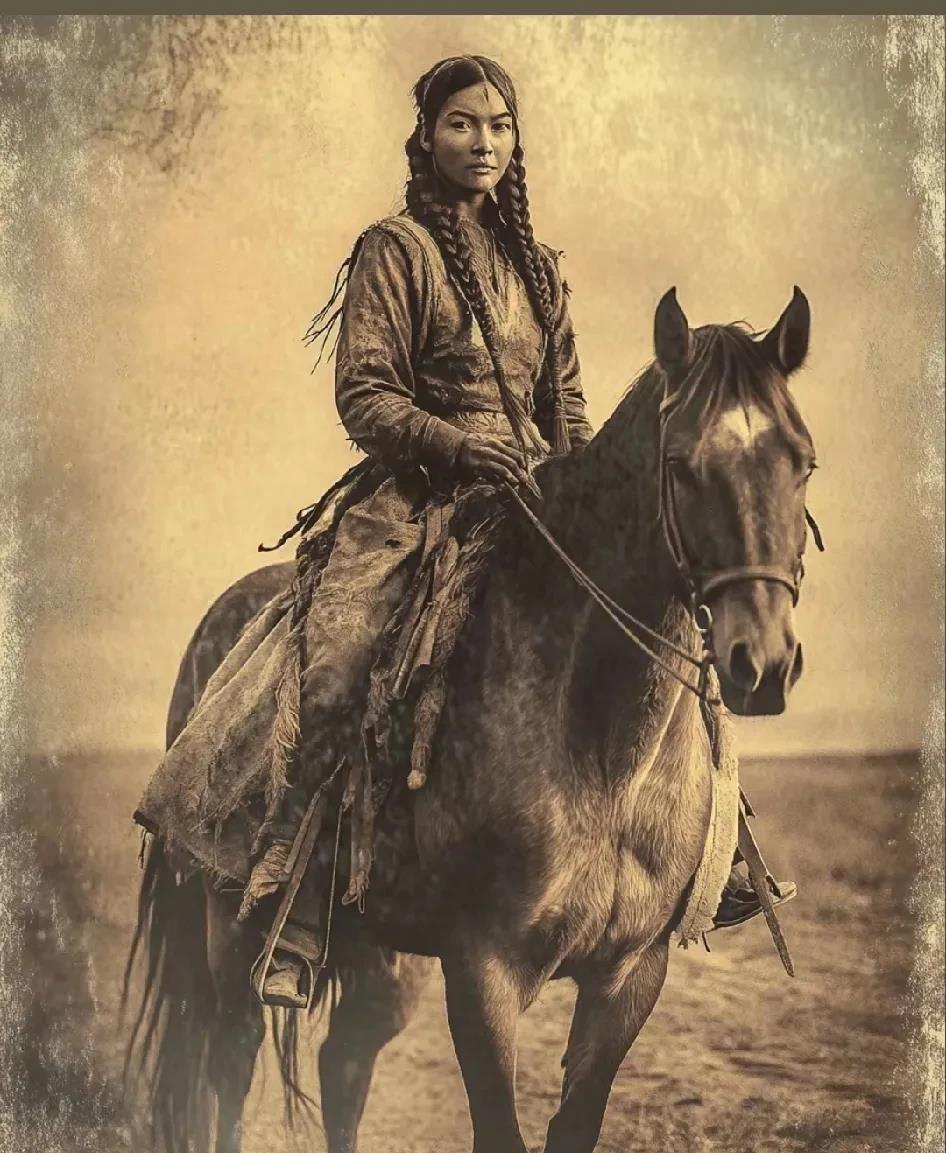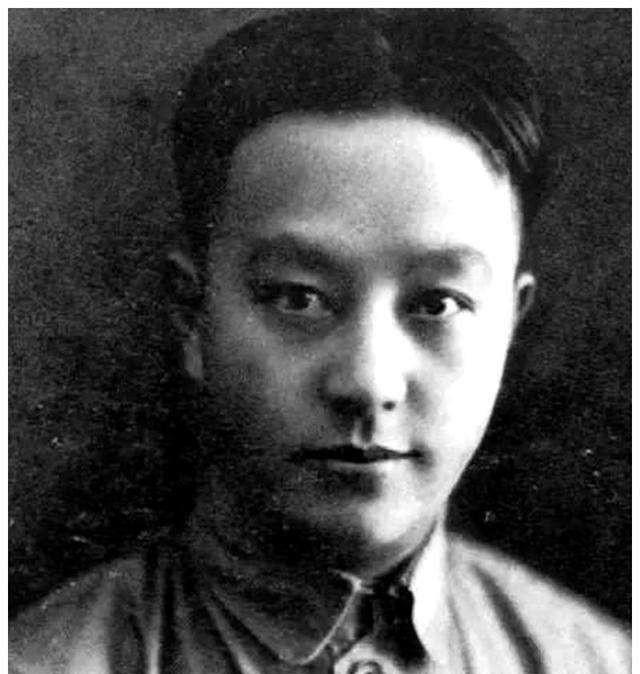1950年,粟裕正在汇报工作,门突然被撞开。李克农冲进来,声音发颤:“粟裕同志,我的小儿子是不是牺牲了?” 1950年,北京的夜色透过厚重的窗帘渗进来,作战室里却灯火通明,墙上那幅覆盖着密密麻麻红蓝箭头的作战地图,被几盏高瓦数的灯照得泛着白光,粟裕手持教鞭,正指着台海方向的标记,向上级细致说明战役部署和部队调动情况。 每一次轻轻敲击掌心,都是节奏分明的提示,屋内的参谋人员忙着在地图上标注新的情报,纸张翻动与铅笔划过的声音交织成一种紧迫的律动。 空气突然被一声剧烈的撞击切断,厚重的门板被猛地推开,撞在墙上发出闷响,所有人的注意力同时被吸引过去,一个熟悉而意外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李克农,衣着整齐却扣错了扣子,面色苍白得像是刚经历了彻夜未眠,脚步急促,仿佛是被某种无法延迟的力量推着走进来,他手中紧攥着一份文件,关节因用力过度而泛白。 室内的气氛骤然凝滞,粟裕停下动作,眼神微微收缩,似乎预感到来者带来的不会是寻常公事,几秒的沉默像被拉长,李克农走到桌前,将那份文件摊开在地图边缘。 薄薄的纸张上,有一份从前线传回的伤亡名单,在某个并不显眼的角落,出现了“李伦”二字,那是他的幼子,一个自1947年参军后便杳无音讯的名字。 三年间,这个名字在军中几乎从未被提及,李伦参军时主动更换姓名,不愿依靠父亲的身份获得任何便利,所在部队又是执行高危任务的特种纵队,常常出现在最前沿的阵地,李克农深知战场的残酷,这样的岗位,任何一次消息中断都可能意味着最坏的结果。 作为情报系统的核心人物,他本可以动用许多渠道去查找,但保密原则与职业操守让他克制了这种冲动,直到这一刻,所有的理智都被压缩成一个急迫的问题,那份名单是真是假。 粟裕仔细看过文件,沉声示意机要员立即调出最新的前线通讯和各战区的伤员收治记录,指令传递得很快,几名值班军官分头行动,有人查阅宁波、厦门等地的后方医院名单,有人联系沿海阵地的联络站,甚至翻查特种纵队的内部花名册。 然而李伦的真实身份被严密隐匿,这让核实过程困难重重,零碎的情报像断裂的绳索,无法立刻拼出完整的画面。 时间在紧张的等待中变得格外缓慢,有人带回消息,说宁波的野战医院收治过一名重伤战士,军籍登记是化名,伤势严重,昏迷中还不断重复战场上的术语。 但因为身份核对不全,这个线索依旧悬而未决,与此同时,前沿的电台报告因战况复杂而中断,缺口无法立刻弥补,室内的气温不高,却让人感到一股闷热的压迫感。 突然桌角的电话铃声打破了沉默,机要员急促的声音从听筒那端传来,报告前沿观察哨在海面上发现一只漂流筏,上面有我军人员。 粟裕迅速下达指令,让对方保持联系并确认身份,李克农没有说话,只是盯着地图上那片被蓝色标记的海域,眼神中闪过复杂的光芒,时间像被绷紧的弦,直到传回确切的信号,生还者正在被接回。 两个小时后,带着海水与火药味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起,李伦被两名战士搀扶着走进来,军装破损,左臂吊着绷带,神情疲惫却挺直了身子。 他的出现,让室内所有悬着的心同时松了口气,父子之间的重逢没有喧哗与言语,李克农只是走上前,动作微微停顿,最终伸手轻拍在儿子的肩上,那一刻,他的表情平静,像是在确认一件重要但早已预料的事实。 表面的平静并不能掩盖情绪的波澜。多年养成的冷静与克制,让他没有当众显露更多,但摘下眼镜时,手背还是轻轻擦过眼角。 有人事后得知,李伦是在执行渡海任务时,因电台损毁与部队失联,被迫躲在礁石缝间,用随身干粮支撑了几天,最后借着一块浮木漂到安全水域,他的身份也在那时终于被确认。 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在战局的宏大背景中或许只是一个插曲,但在当事人心中,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多年后回望,那一晚的作战室,不只是部署与数据的汇集地,也是一次无声的情感交锋的见证,战争的冷峻外表下,依然包裹着最炽热的牵挂与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