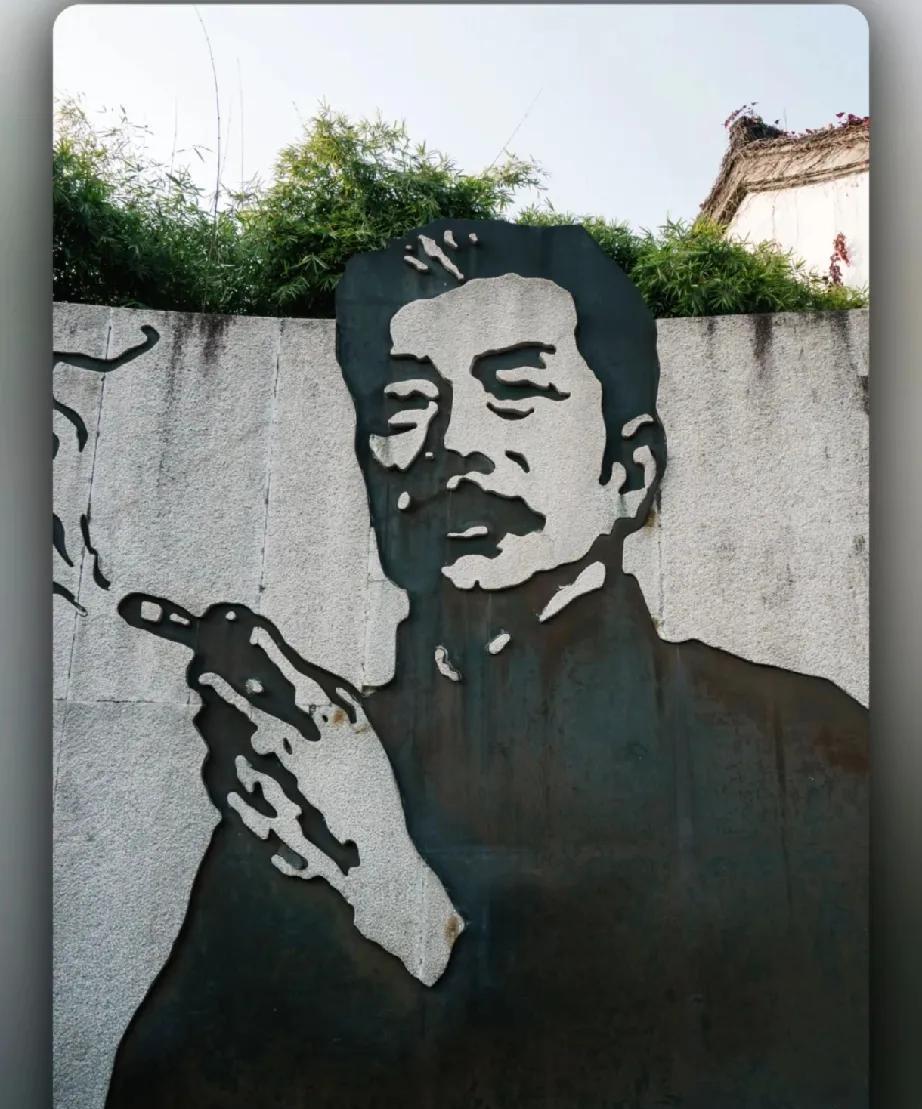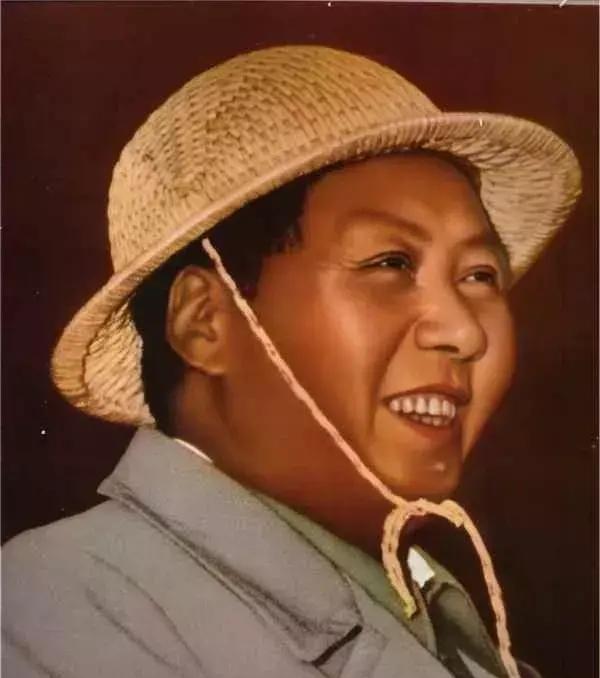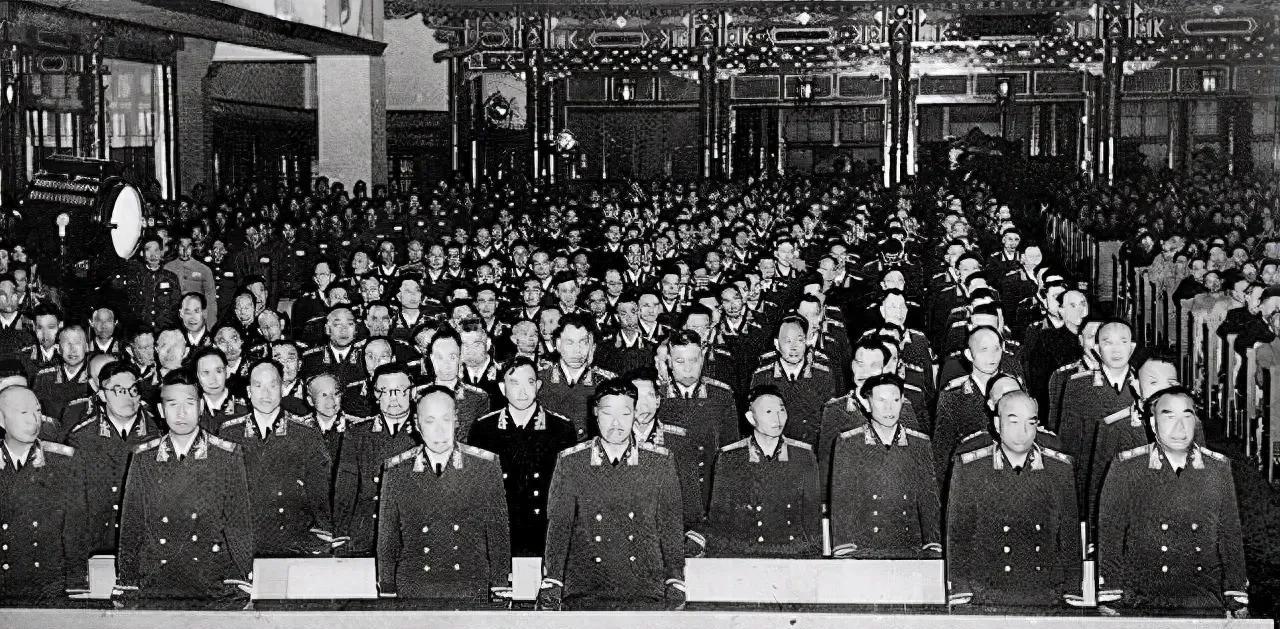747年,宰相李适之望着手中的毒酒,哭着说:“我爷爷李承乾谋反被废,我辞官还自以为是可以避免灾祸的,没想到李林甫还是不放过我啊。”说完,一饮而尽。 毒酒滑过喉咙时带着铁锈似的腥气,李适之攥着酒盏的手没松,视线却慢慢模糊了。窗外的石榴树是他去年亲手栽的,这会儿新抽的枝芽还嫩生生的,倒让他想起爷爷李承乾被废那年——也是这样的春天,东宫的海棠落了一地,他爹李象抱着年幼的他躲在夹道里,听着宫墙外的金吾卫甲叶响,声音抖得像风中的蛛网:“记住,咱李家往后再不能争了。” 他原是记着的。年轻时考中进士,只拣了个地方官做,在金州当刺史那几年,日日盯着粮仓的账簿,连下属递来的绸缎都没敢收过。后来玄宗召他回京,他站在大明宫丹陛底下,看着龙椅上那个鬓角发白的皇帝,膝盖都在打颤。那会儿李林甫刚坐上宰相的位置,在紫宸殿门口撞见他,笑着拍他的背:“李大人是皇室贵胄,该在朝堂上帮陛下分忧才是。”他当时只觉得那笑声里裹着冰碴,却没敢躲。 做宰相的头一年还算安稳。他学着李林甫的样子,在奏疏里捡些“五谷丰登”“边军安稳”的话说,朝堂上遇见争论,也总低着头不吭声。可玄宗偏喜欢问他意见,有回讨论漕运的事,他被问得急了,顺嘴说了句“江南漕船可再增十艘”,话音刚落就见李林甫端着茶杯的手顿了顿。散朝后他回府翻出《汉书》,盯着“飞鸟尽,良弓藏”那行字看了半宿,后颈的冷汗把衣领都洇透了。 转过年来就开始不对劲。先是他举荐的几个县令被御史弹劾“贪墨”,查来查去查不出实证,却生生把他的脸面磨掉了一层。接着宫里传话说玄宗赏了李林甫一幅《霓裳羽衣图》,他听见消息时正在书房写《左氏春秋注》,笔杆“啪”地掉在砚台上,墨汁溅得宣纸上一片黑。 他连夜写了辞官奏疏,把“体弱”“思退”的话说得恳切,第二天递上去时,玄宗盯着他看了半晌,慢悠悠地说:“你是李承乾的孙儿,朕信你。”他跪在地上磕头,额头撞在金砖上发疼,心里却比坠了铅还沉——帝王的“信”,从来不是护身符。 辞官后他搬到长安城外的别业,每日种竹、读书,连城门都少进。有回侄子来看他,说李林甫在朝堂上提“宗室不宜闲置”,他手里的锄头“哐当”掉在菜地里,盯着田埂上的蚂蚁看了半天,突然笑出声:“躲是躲不掉的。”那天晚上他让家仆烫了壶酒,自己坐在月下喝,喝着喝着就哭了——他爷爷李承乾当年是想抢皇位,落得个废黜身死;他这辈子只求安稳,怎么还是逃不过? 前几日李林甫派人送“赏赐”来,是一坛据说是“剑南贡品”的酒。送酒的小吏笑得客气,眼神却像刀子似的刮他。他接过酒坛时没手抖,只摸了摸坛口的封泥,心里透亮——该来的终究来了。家仆劝他“别喝”,他摆摆手,把人都打发出去。 独坐在书房里,看着墙上挂的李承乾手书的“守拙”二字,忽然想起小时候爹教他写字,笔尖总往“稳”上引,原来从那时起,他们李家就只剩“守”这一条路,可连“守”都守不住。 毒酒的后劲来得快,五脏六腑像被烈火燎着疼。他趴在书桌上,手指抠着桌沿,指缝里渗出血珠,视线最后落在窗台上那盆刚开的兰花上——那是去年从终南山挖来的,本想着今年春天能开得热闹些。意识散了的时候,他好像听见远处传来长安的钟鼓声,还是那么悠长,只是这声音里,再没有他李适之的位置了。 后来有人说,李林甫之所以不放过他,是怕他哪天被玄宗重新召回朝堂;也有人说,是他身上流着的李承乾的血,本就让帝王和权臣都放不下心。其实哪用那么多缘由?在皇权的棋盘上,他这样的“宗室旧人”,从来都是可弃的棋子。你想退?可棋盘就这么大,只要还在局里,哪怕缩在角落,也迟早会被棋子碾过去。 参考书籍:《旧唐书·李适之传》、《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