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为何是江南的第九兵团?偌大北方,再无战略预备队可用 1950年11月7日黎明,鸭绿江边传来一句低沉的问话:“司令员,我们真的要穿着这身薄棉衣过江吗?”寒风卷着江雾,吹得军帽上的红星隐约发白。宋时轮站在岸边,只说了两个字:“立即!”短短的对话,定格了第九兵团即将投入东线作战的那一瞬间,也把一个疑问留给后人——为什么偏偏是来自江南的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要在零下三四十度的长津湖迎战美军陆战一师? 要想解释这个“南兵北战”的布局,得先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兵力分布。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时,第一至第四野战军全部越过长江,重任是肃清残敌、接管新政权。西南尚未平定、西北仍在剿匪,东南沿海则要筹划攻台。这样一来,最精锐的主力大规模滞留在长江以南,而黄河、长城一线留给各军区的多是地方师团,缺枪、缺炮,也缺训练。 中央并非没有预案。1950年初,军委挑选了第38、第39、第40三个王牌军撤出广西、湖南,回师河南,准备组建全国机动的战略预备队——后来人们熟知的“东北边防军”。这支部队到7月就全部北上,25万人开到丹东、辽阳,成了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第十三兵团。代价是,华北与东北的纵深里瞬间空了大片:一个能快速投送的大兵团,瞬间找不到了。 江南的第九兵团因此进入视野。它从未担负具体警备区的行政任务,番号完备,装备较新,司令部也没改编成地方军区,符合“随叫随到”的标准。再加上军委原本计划让粟裕挂帅出征,不免要搭配熟悉的三野部队,这一点在早期文件里有迹可循。于是,驻在苏南、刚结束攻台训练的第20、第26、第27三个军,8月起陆续北调山东泰安一带,以铁路运力为支点,成为第二梯队预备队。 剧变很快到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一路狂飙,东线的第十军沿海岸插向咸镜北道,威胁志愿军西线侧后。10月底,彭德怀电示军委:如无强力封堵,美军可能在两周内抵达江界。在这种背景下,原定在吉林梅河口换装的第九兵团被紧急改令:不整训,不换装,直接从辑安、临江口子夜过江,切断美陆战一师北进通道。宋时轮只争取到三天时间,但到沈阳时,厚棉服尚在车站仓库,棉鞋、棉帽更在梅河口。运输主任贺晋年焦急地说:“再晚半小时,机场的灯就亮了。”列车没等补给就继续北上,结果可想而知。 行军困难不仅因温度。东线此前没有己方补给线。九兵团每名战士只能背四天口粮,两百发子弹,夜里摸黑翻山,白天隐蔽林间。统计数字枯燥:长津湖一役,战斗减员两万余,非战斗减员超过三万。但真正刺痛老兵记忆的,是一支支小队在雪窝里保持射击姿势再也没动——“冰雕连”只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符号。 人们常感叹:如果换做北方部队,是否能多抗几度?答案未必乐观。那年冬季的盖马高原气温达到-42℃,连美陆战一师也因油品冻结被迫弃车。问题根源仍旧是战略态势:北部纵深兵力空虚,能担任第二波投入的,只剩驻山东、番号完整的九兵团。调谁都要在严寒作战;调九兵团至少能在最短时间堵上东线缺口,这是当时高层唯一能做出的“最优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第九兵团并非全是江南子弟。第26军、27军主体来自山东,第20军则起家于闽东。可即便有一半山东兵,南方作战经验居多,对极寒同样缺乏体会。有人形容:行军第一晚,步枪机头与金属皮手套“焊”在一起,撬开时连带皮肉。一支部队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完成穿插、包围、美军机械化反击,再坚持二十多天,这本身已是奇迹。麦克阿瑟后来在听证会上无奈承认:“中国人在我们最不可能承受的地段和季节发动了战役。” 换个角度,如果没有第九兵团,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在西线能否集中兵力发起第二次战役?恐怕难以保证。东线若丢,西线部队侧后受敌;江界若失,军事与政治意义更极其严重。当时不惜牺牲的决策,保住了整个第一次、第二次战役的大框架,也为随后几年的拉锯奠定了基调。 1952年9月,第九兵团奉命回国。车队抵鸭绿江大桥前,宋时轮特意让全体下车,面向长津湖方向默立。他脱帽,鞠了一躬,又鞠了一躬。同行的警卫员记得,那位向来硬朗的将军,面颊被江风吹得绯红,眼眶却早已湿透。此刻不需要任何口号,也无需抒情——答案就写在他那一身褪色军棉服上:之所以是江南的第九兵团,因为此前的北方,已倾其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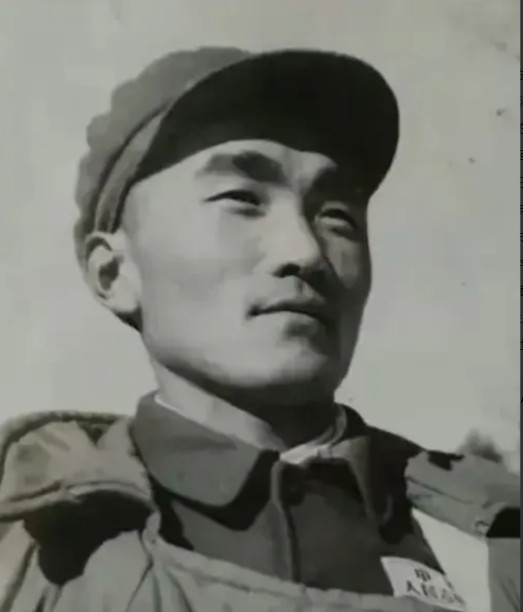


苏米
[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