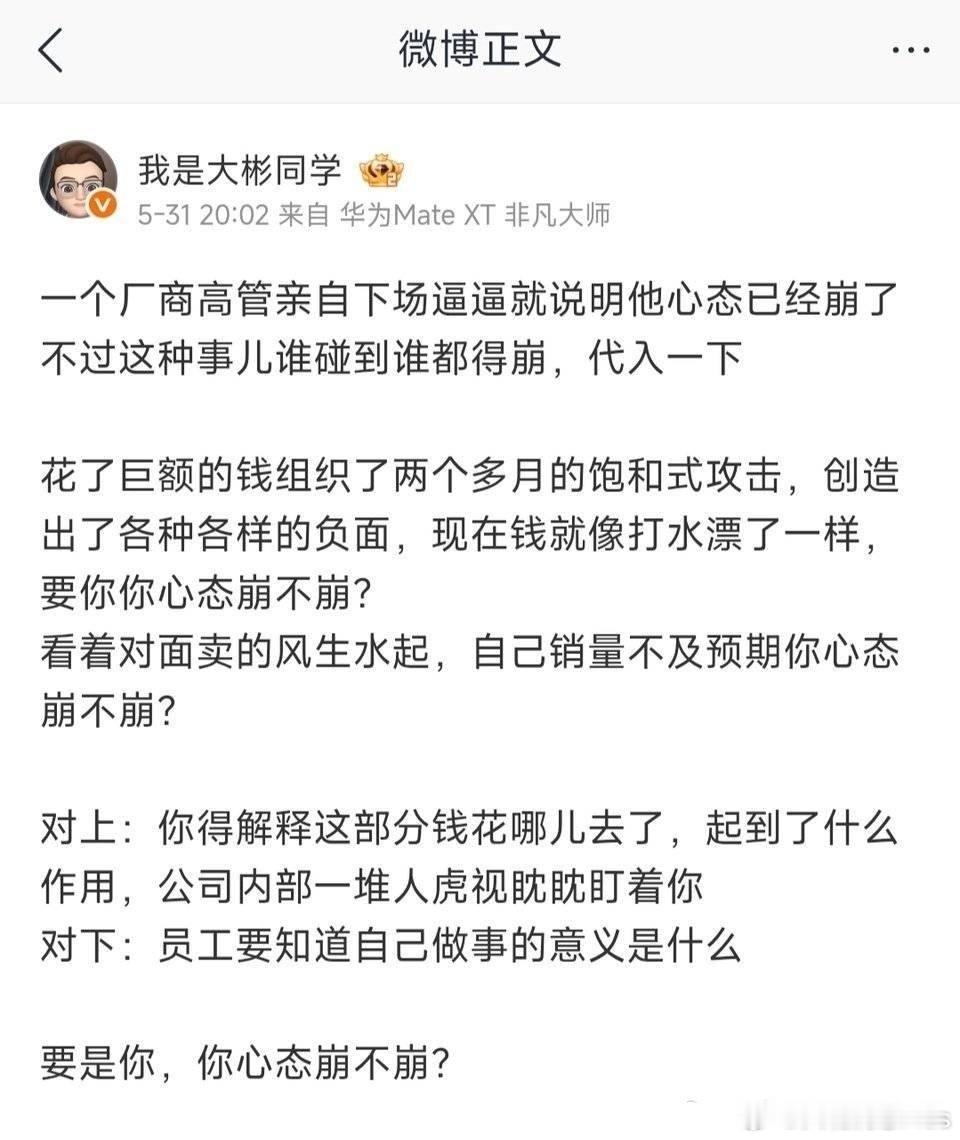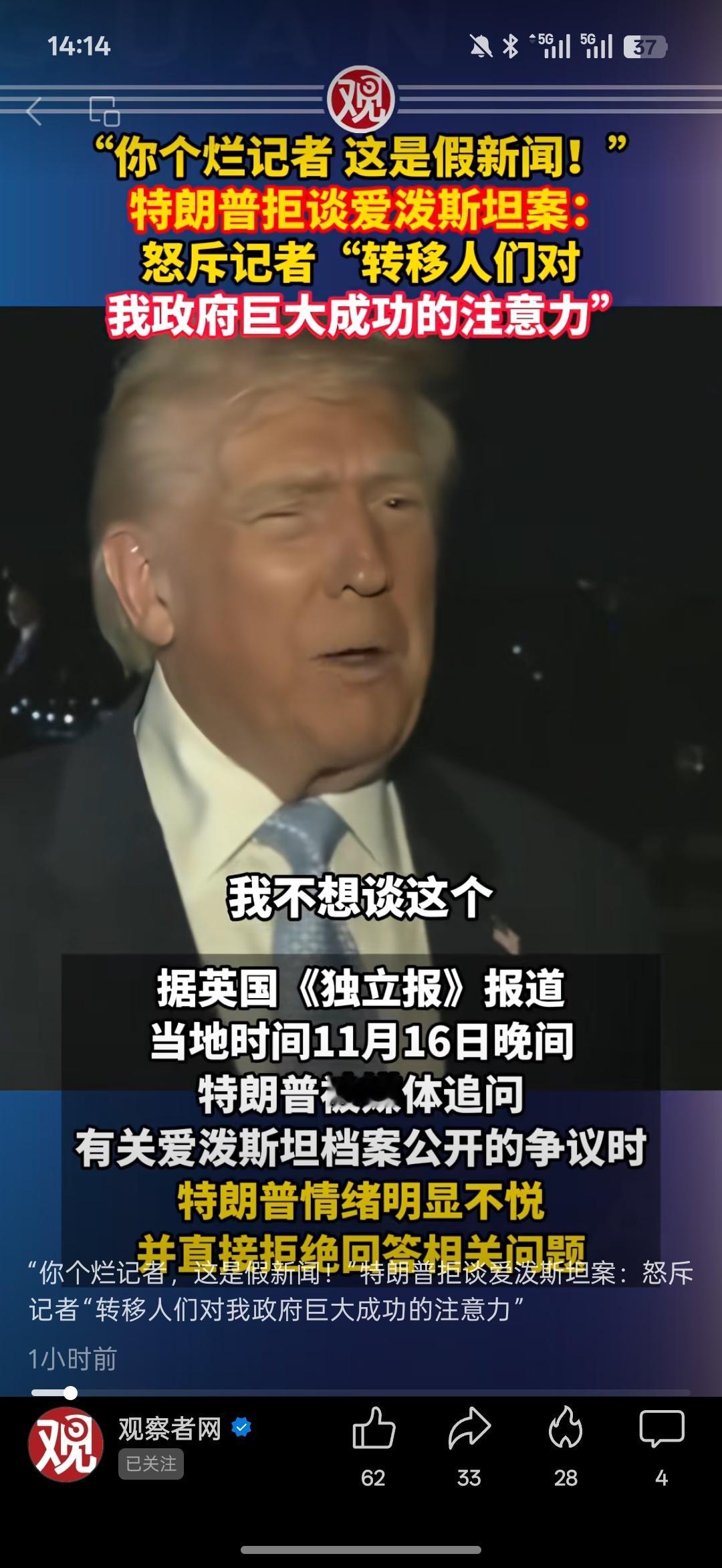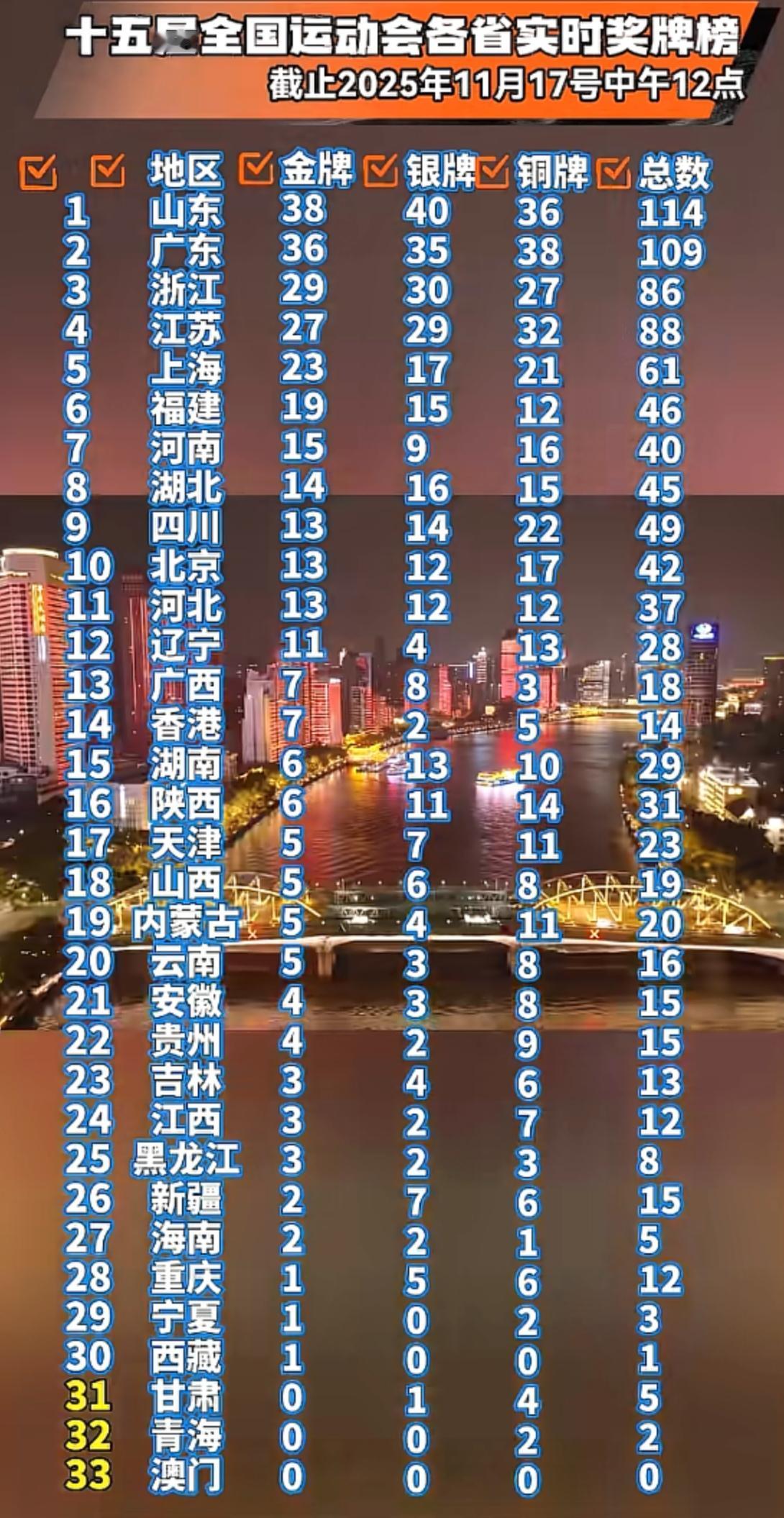我曾经养过一条苏牧,给它起的名字便叫做阿牧了。一天早晨我牵着它到村口河边的树林里溜达时,碰上了村里放羊的阿b,只见他双手揣在破棉袄的袖筒里,抱着鞭子呲着牙冲着我和阿牧大喊着:“阿呆、阿呆!”见我没有理他,他又不停的喊上了:“阿呆、阿呆!”我于是停了下来,愣愣的看着他问道:“喊谁呢?”他咧着嘴笑着答道:“喊你们家的狗呢!我这么喊它怎么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呢?” “谁跟你说我这狗叫阿呆呀?” “我有时听见你就叫它阿呆呀。” “我什么时候叫它阿呆啦?我的狗叫阿牧。”我白楞了他一眼。 “哦,对,叫阿牧,我记错了,记错了。”他依旧呲着牙、咧着嘴,傻乎乎的笑着。 “你喊它干嘛?” “没事儿,我就是喜欢它,你说我要是有这么一只狗,我放羊是不是就轻趁多啦?” 什么?轻趁?你老板要是有这么条狗,你怕是就得失业了。我心里这么想,但没说出口,只是冲他笑了笑,牵着狗走了。 阿呆,他为啥要叫阿牧阿呆呢?不用想,我瞬间也就明白了。他一定把阿牧想成了阿木,而木和呆又常常被人们连在一起,于是乎便由木想到了呆,在忘记了阿牧的名字时,就把呆字喊出来了。这个呆子呀! 阿b姓钱,叫钱老六,阿b这一尊称,是我给他起的。为何这么称呼他呢?因为在我眼里,这家伙跟阿Q是很有一拼的。 按照阿Q自己的说法,他本姓赵,皆因为赵太爷的儿子考上秀才时,他不仅感到光彩、自豪感油然而生,还兴奋、得意的过了头,以赵家长辈自居起来了。结果伴随着“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而来的那记耳光,打的他连姓氏都没有了。以至于鲁迅先生给他做传时因为姓名还费了一番周折。而我们村里的阿b呢,只要有人夸他放的羊时,他瞬间便会得意起来,腆着脸回应道:“你也不看看我这羊是谁养的!谁放的!咱们村里虽说有三四家养羊的,可谁有俺们老板的羊多?谁的羊有俺放的羊肥?”阿d的老板是京城人,年轻时曾在村里插过队,后来仗着他老爹的关系帮他联系了几家大企业,用他送来的煤。于是他干了些年有定点销路的煤贩子,挣了些钱后,又被他爹调到某机关吃官饭去了。他回村里养羊,并不全为了卖羊赚钱,一是为了显摆,找一种荣归故里的感觉。二是逢年过节时杀些羊带回去送送用得着的人,给自己围下点人脉。除了有时周六日他开车回来看看,平日里都由他雇佣的两个羊倌儿帮他打理这些羊。至于说那个阿b还算不上是个羊倌儿,也就是一个拿着鞭子跟在羊群后面的羊伴子。羊赶到村旁河边的树林里后,羊倌儿就溜达回去了,由阿b看着羊吃草,这也就是阿b最为得意的时候,可以逢人就一口一个我的羊、我的羊的自豪起来了。 第二,鲁迅给阿Q立传时,尽管为这一名字做了一些解释,但我仍以为这个Q下面的小尾巴,与前清时期男人后面拖的那根小辫子十分相似。受此影响,我便想到了b这个字母。他脑后虽没有小辫子了,但自我膨胀起来后,心中的那条小辫子绝对是要翘得高过头顶了,所以取名为阿b,也自然就觉得十分的恰当了。 其实甭管是当年的阿Q还是今天的阿b,在我们的生活中绝非少见,所以我也早就见怪不怪了。今天之所以写他,是因为他喊出了那句阿呆…… 呆者,何为呆?小时候院儿里王奶奶曾经说过:遇见傻子,千万不要说他傻,因为他最忌讳的、就是那个傻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