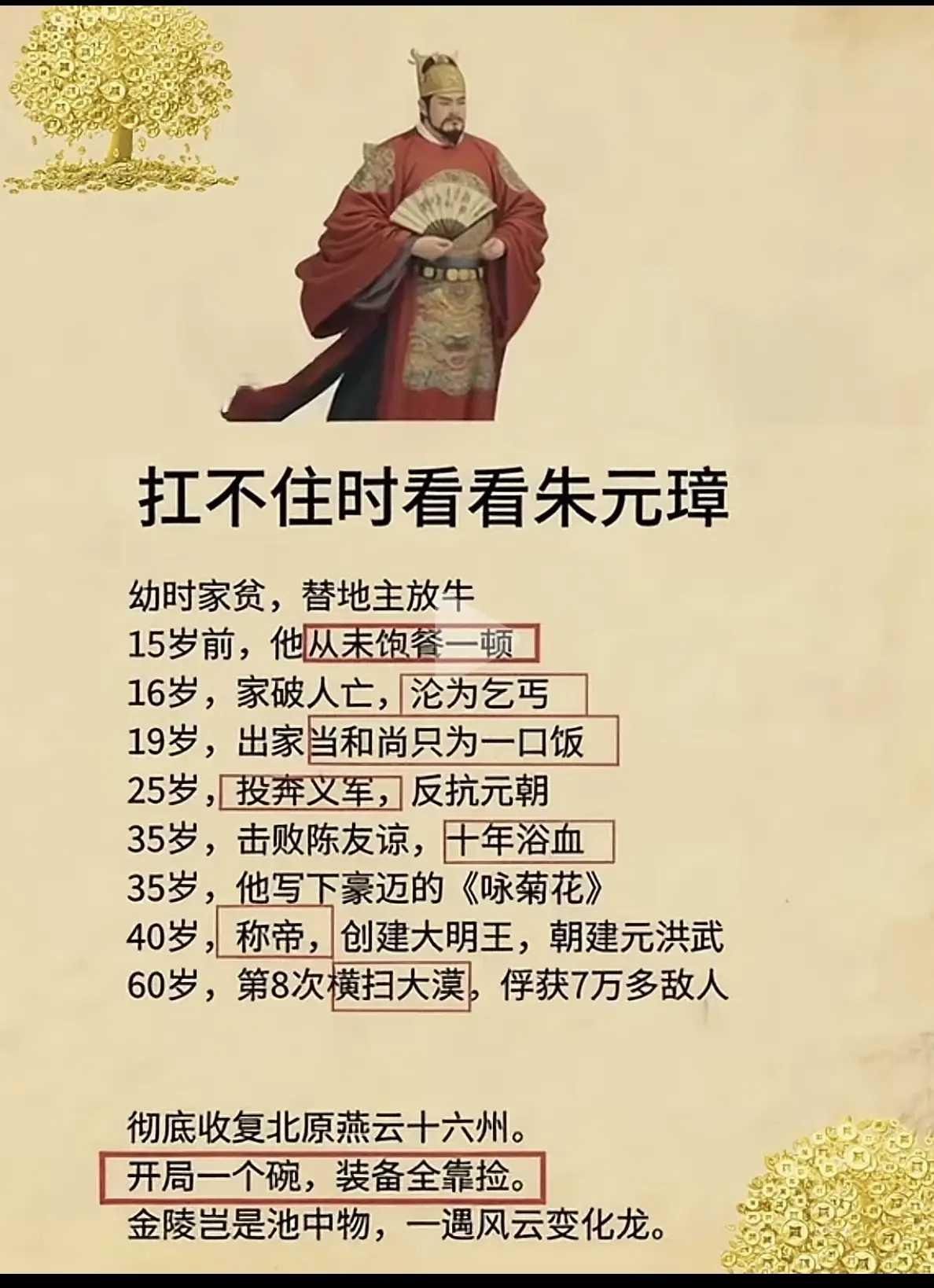1395年,68岁的朱元璋去看望70岁的汤和,在此之前,朱元璋刚杀了宋国公冯胜,明朝开国六公爵一个不剩,汤和用一种乞求的眼光看着朱元璋,好像在问:“陛下,那么多老兄弟,真的一个不留吗?” 1395年冬天,南京飘着雪。68岁的朱元璋拄着楠木拐杖,站在奉天门的石阶上。他头发全白,背驼得厉害,只有眼睛还像年轻时那样锐利,能穿透寒气。 贴身太监走过来,声音放得很轻,说,陛下,去汤国公府的马车备好了。朱元璋点点头,没说话。他心里清楚,半个月前刚赐死宋国公冯胜,当年开国封的六个公爵,已经一个也没有了。 马车碾过积雪,车轮咯吱响。朱元璋靠在软榻上,闭着眼,脑子里全是四十多年前的事。那时候他刚从皇觉寺出来。汤和比他大两岁,已经在郭子兴手下做了千户,却每次见他都躬身喊“朱兄弟”。 有次队伍被元军困在濠州城外的山谷里,三天没吃一粒米。大家都快撑不住的时候,汤和偷偷从怀里摸出半块麦饼。却塞到朱元璋手里,只说,你脑子活,得活着带我们出去。那半块饼的味道,朱元璋记了一辈子。 马车停在汤和府前。这座宅子是朱元璋十年前赐的,青砖灰瓦,不算奢华,但很规整。可此刻府里冷冷清清,连个站岗的家丁都少见。汤和的长子汤鼎穿着素色袍子,跪在雪地里,膝盖下的雪已经渗进衣服里。他见朱元璋下车,连忙磕头,声音发颤。他说,家父已经三天没进水米了,罪子…… 朱元璋伸手把他扶起来,指尖触到汤鼎的胳膊,冰凉一片。他没多问,只说,带我去见你父亲。 穿过庭院,药味越来越浓。进了卧房,帐幔半垂着。汤和躺在床上,颧骨高高凸起来,嘴唇干裂,嘴角还不时流出口水,把枕边的锦缎都浸湿了。 听到脚步声,汤和慢慢睁开眼。他的眼珠很浑浊,转了半天才落在朱元璋身上。看到朱元璋的瞬间,他的眼睛亮了亮,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像是想说话,却怎么也发不出完整的声音。 朱元璋挥手让所有人都出去,连贴身太监都被赶到了门外。他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床边,声音放得很轻,用的还是当年在濠州时的称呼。他说,汤和,我来看你了。 汤和眨了眨眼,眼泪顺着眼角慢慢淌下来。朱元璋掏出随身的手帕,替他擦了擦脸。擦完脸,他没再绕弯子,直接说起了冯胜。他说,冯胜私藏兵器,还在府里议论允炆的不是。这江山将来是允炆的,谁要是敢动心思,我就不能留他。 他又提起其他几个兄弟。徐达死得早,洪武十八年就病逝了,倒没赶上后来的事。常遇春性子急,洪武二年打胜仗回来,半路上就病死在柳河川,他儿子常茂不成器,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李善长是文臣里的老大哥,却跟着胡惟庸谋逆,想换个皇帝。蓝玉更不像话,打了胜仗就骄傲,在军里私自提拔人,朝廷的规矩都不放在眼里。这些人,都被他杀了。 朱元璋看着汤和,继续说。大哥,你跟他们不一样。洪武二十一年,你主动来找我,说自己年纪大了,打不动仗了,想把兵权交回来,回老家养老。你还跟我要美女、要财宝,故意装出一副贪图享乐的样子。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也懂君臣之间的规矩,从不多占一点权。 汤和的手动了动,像是想抓住什么。朱元璋连忙把自己的手递过去。汤和枯瘦的手指紧紧攥住他的手,力气不大,却抓得很牢。 朱元璋的声音突然哑了。他说,标儿37岁就走了。允炆那时候才15岁,性子软,没见过刀光剑影。我这身子一天不如一天,要是不把这些能力超群的功臣除掉,允炆根本镇不住他们。我是朱家的皇帝,得守住朱家的江山。 汤和似乎听懂了。他用力抬起另一只手,先伸了两根手指,颤巍巍地晃了晃,又用小指头指了指朱元璋,再指了指自己。 朱元璋的眼眶一下子热了。他知道,汤和是在问,是不是就剩我们两个了。汤和也是在说,当年在濠州的时候,我们这些兄弟,都听你的。 朱元璋握紧他的手,声音带着哽咽。他说,你安心走吧。到了那边,替我跟兄弟们,说声对不起。不是我不念兄弟情分,只是我坐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事没得选。等我百年之后,再跟你们赔罪。 汤和眨了眨眼,眼神慢慢平静下来。他攥着朱元璋的手,一点点松开。朱元璋探了探他的鼻息,已经没气了,手也慢慢凉了下去。 朱元璋站起身,走到窗边。外面的雪还在下,院子里的树枝都被雪压弯了。他对着门外喊了一声,声音很沉。他说,汤和一生忠勇,按王爷的规格办后事,追封东瓯王,谥号襄武。他的子孙,世袭爵位,永享福禄。 回宫的路上,马车里很安静。朱元璋靠在软榻上,闭着眼,却没睡着。回到皇宫,他没去乾清宫,而是径直走到奉天殿,坐在龙椅上。 殿外的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落在他身上。金色的龙袍闪闪发光,却照不到大殿角落里的阴影。朱元璋看着空荡荡的大殿,喃喃自语。徐达走了,常遇春走了,冯胜走了,现在汤和也走了。你们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这年十二月,汤和下葬。朱元璋没去送葬,只是站在皇宫的城楼上,望着汤和府的方向。他站了很久,直到天色暗下来,雪花又开始飘,才慢慢转身回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