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岁老小孩:黄永玉——把岁月熬成糖霜,把死亡写成童谣 北京在六月交出最后一场槐雨,像为他洗净长街,好让那辆红色法拉利一路飞驰到云端。人们说黄永玉走了,我却只信他贪玩迷路,叼着烟斗去银河边给星星起绰号——上帝想留他当首席捣蛋鬼,他嫌天堂规矩太多,一踩油门,把九十九年的笑声撒成漫天流萤。 凤凰的水车还在转,却再无人把石板巷走成电闪。十二岁的赤脚少年,书包里装着偷摘的野桃和一本《楚辞》,逃学,是为了去听沅水怎样把屈原的句子唱成民谣。十四岁寄身闽南山坳,木屑纷扬如早雪,锯条拉出肖邦的升C,他在刨花香里嗅到远渡欧洲的潮汐,于是把第一朵木刻玫瑰献给战火纷飞的年代。三十二岁,阿诗玛从云南的云雾里站起身,青铜色的手臂举起整座高原,他把亿万年的岩溶画成一声暴烈的叹息,全国都在传颂,他却转身去景德镇烧夜壶——壶口歪斜,像对世界做半个鬼脸。五十岁,他考下驾照,像领取一张准许胡闹的出生证;七十岁,背起行囊去意大利写生,把威尼斯清晨的薄雾熬成一碗糯米酒;八十岁,穿大红西装登上时尚杂志封面,银髯与电眼并列,像雪峰上突然升起朝霞;九十岁,一脚油门,法拉利呼啸穿过京城黄昏,红灯被他闯成漫天礼花。 有人怒斥他败坏国画,墨色太艳,像打翻胭脂铺。他懒洋洋吐烟圈:“谁说这是国画?别糟蹋了人家清誉。”随即补刀:“谁再乱扣帽子,我就告他。”一句话,把堂皇的审美法庭拆成纸扎戏台。十年动荡,他被押进牛棚,每日功课是挨鞭,生日也未能豁免。回家,却笑着报账:“今天224下,比昨天便宜两鞭。”夜里,他在煤油灯下画黑梅,墨汁里掺一点血,竟开出比夜更亮的锋芒。 湘西酒厂破产,工人连工资都发不出。他随手勾了个衣衫褴褛的醉汉,题一句“不可不醉,不可太醉”,酒鬼酒横空出世,一年利税翻十倍,全县炊烟再起。家乡河被化工厂染成铁锈红,八十岁的他拍案而起:“老子去搞他们一下!”连夜带人砸了办公室,像少年砸碎恶霸的玻璃。钱钟书说曾被弟子反噬,他撸袖子:“早告诉我,揍他一顿替你出气!”狂狷之下,是滚烫的侠义。 他最怕的不是死,是死前没把玩笑开够。于是提前给死亡写好剧本:骨灰冲进马桶,告别式就在厕所,按下冲水键,“哗”的一声——人生谢幕,干脆利落。他还想活着就开追悼会,躺椅放中间,喇叭喊:“来,夸我!”悲伤被他逗得破涕为笑,泪珠尚未落地,就被烟斗里的火星烤成闪闪发亮的星尘。 世人总爱把老年描成灰白:保温杯里泡枸杞,广场跳着慢三。他偏把晚年染成大红,法拉利引擎轰成春雷,告诉三亿即将老去的中国人:年轮可以折成纸飞机,皱纹可以叠成纸鹤,白发?那是雪落在火焰上,越冷越旺。他上午写书,下午画画,周末看《非诚勿扰》,说要研究年轻人怎样把爱情拆成快递。九十岁写自传,只到少年篇,因为后面“还在进行式”。 我们读他,读到自己的怯懦:敢不敢在三十岁的饭局说“我不干了”;敢不敢在五十岁的夜里去考一张驾照;敢不敢在八十岁的清晨穿大红色上街;敢不敢在每一次被生活抽鞭子时,回家数给爱人听,然后相信“时代不会永远这样”?他把“自我”磨成一把薄薄的柳叶刀,划开集体叙事的厚茧,让我们看见:原来人可以这样大写。 黄永玉走了,却把“高兴就好”四个字贴在夜空,像四颗最倔的星,闪给仍在地面皱眉的我们。下次当你犹豫要不要把日子过成别人眼里的正经,就想想那个九十九岁的老小孩——油门一踩,烟斗一扬,留下一串尾气,像给世界做了个鬼脸:“别急着老,我先去前面玩。” 于是,我们终于可以含泪带笑地承认:原来衰老不是投降,而是把岁月熬成糖霜;原来死亡不是终点,而是把童谣唱给星辰听。而他,那个最会捣蛋的老小孩,已开着红色法拉利,把最后一声笑,轰然驶入银河。 百岁小老孩 九旬老童 黄永玉百年画展 黄永玉上海展 黄永玉画展 黄永华为何出名 黄永玉旧居 老顽童绘画 黄永日 黄永玉文华园 黄永健 黄永志 黄永叶 儿童老艺术家 黄永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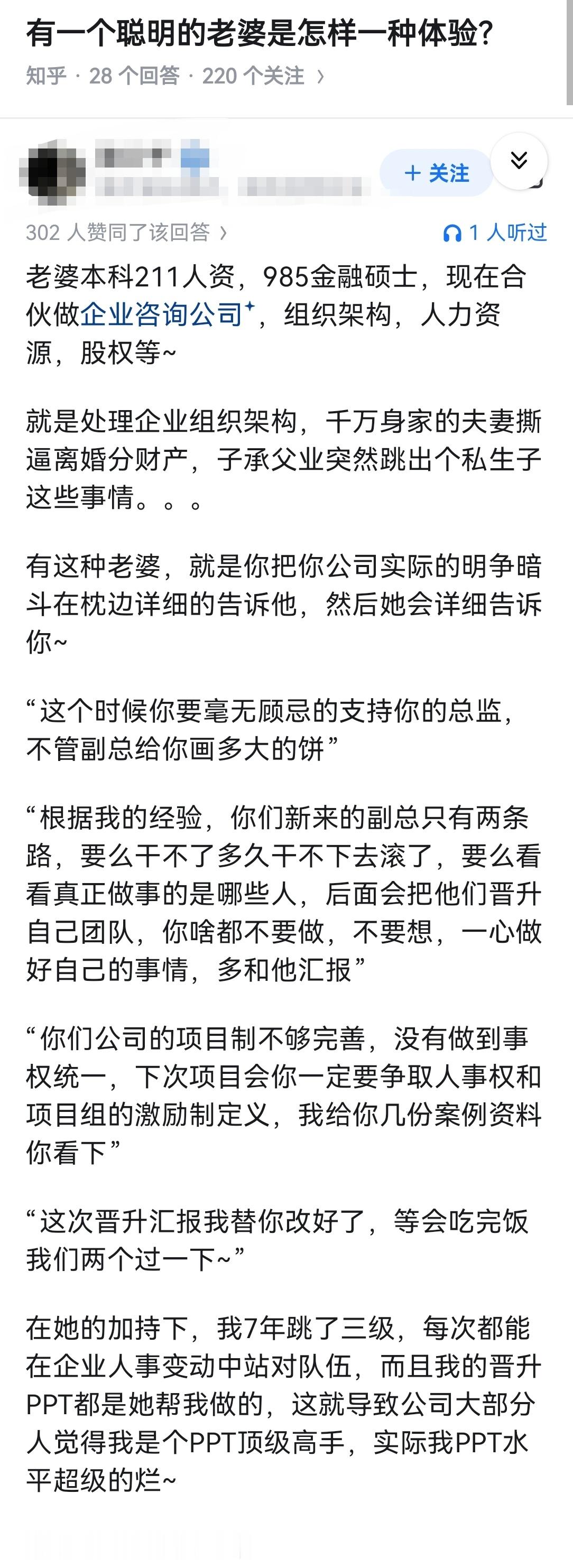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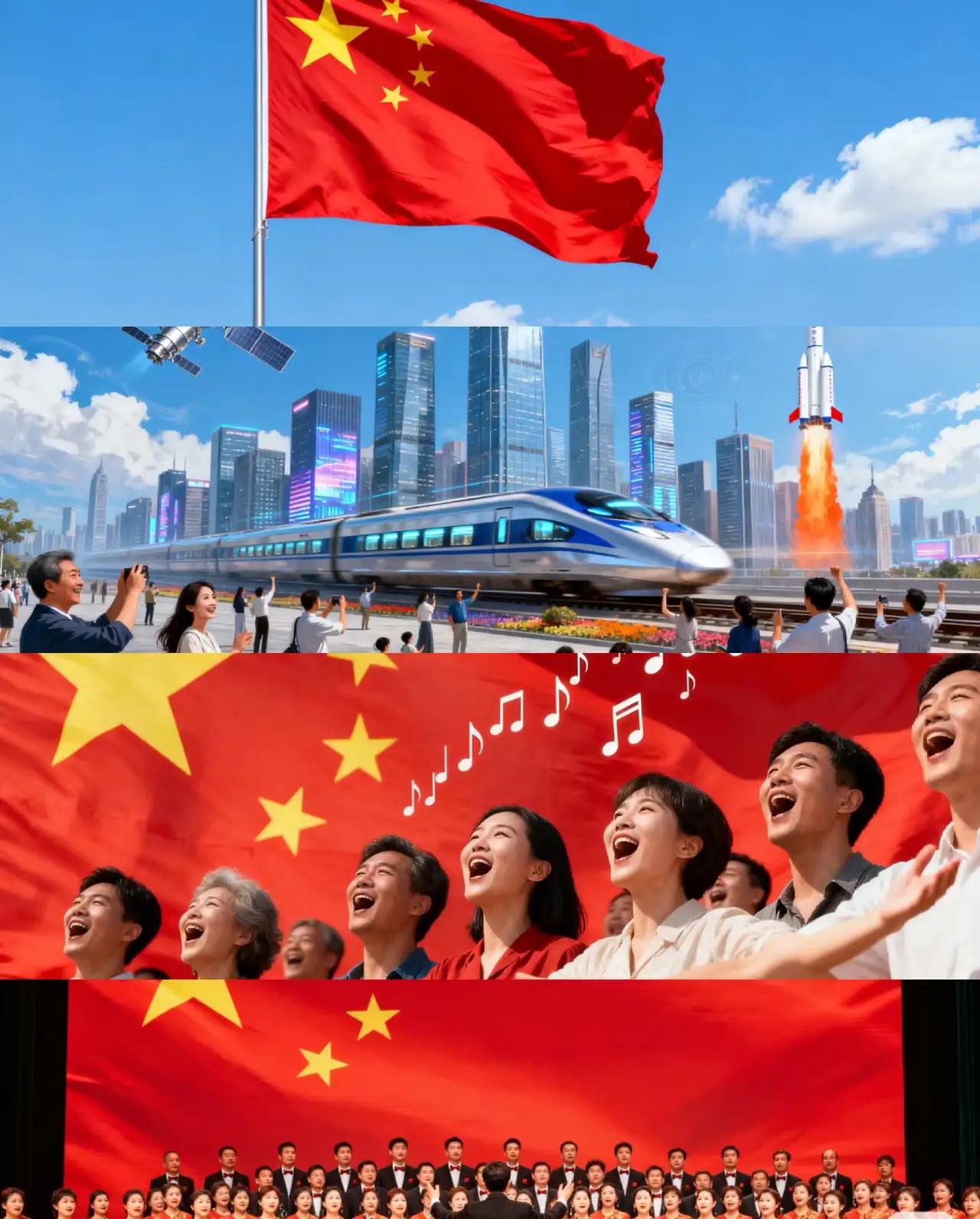


![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太多了[6]](http://image.uczzd.cn/8616648195145734787.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