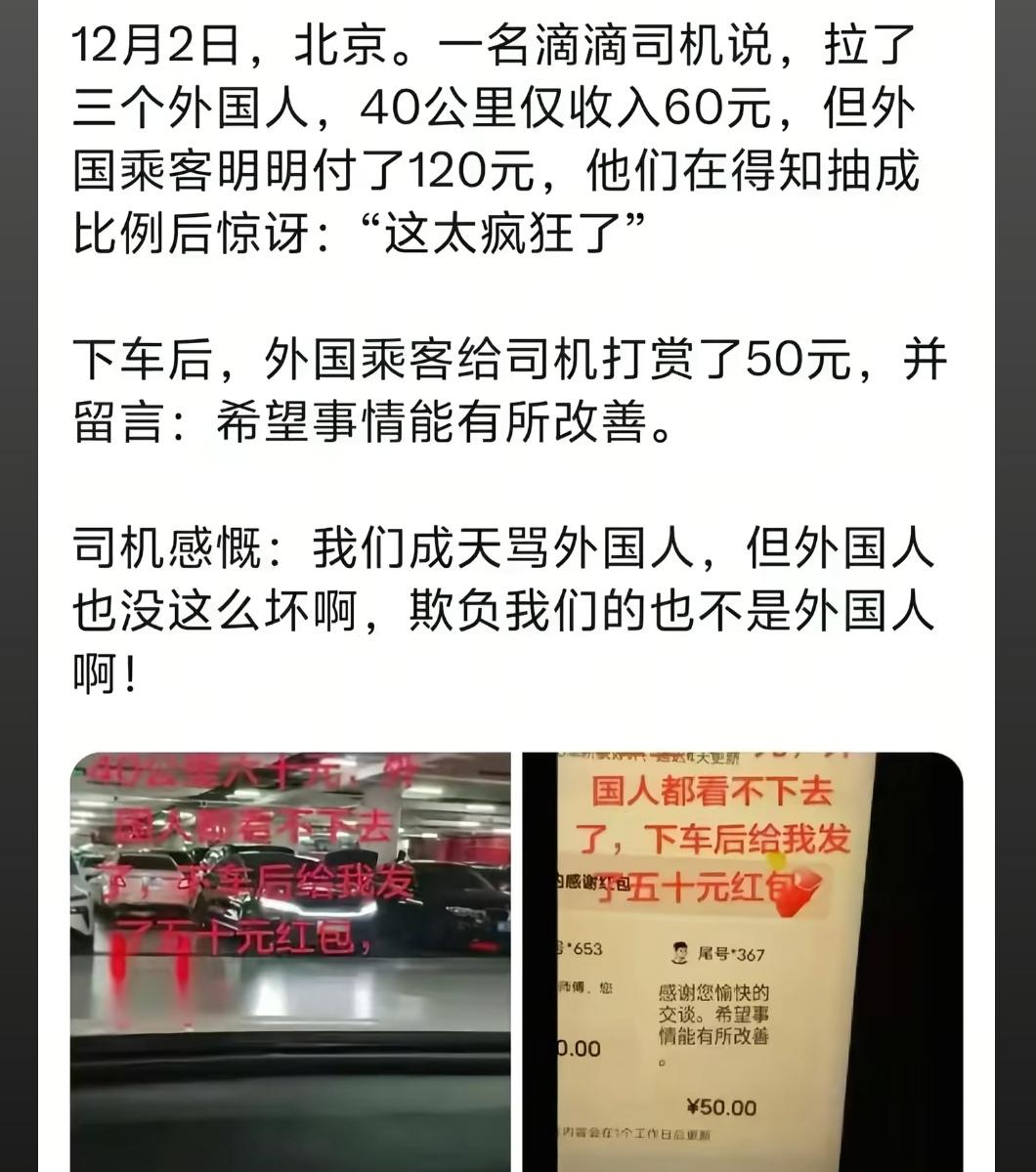1999年,江西一位年轻人卖掉了加油站,用钱在北京郊区买了600亩地,赚了50多亿,后来他为了追求女明星,疯狂花了1.2亿买古董,结果还不上尾款,最终被拍卖公司起诉。 命运有时候像个那种特别爱开玩笑的蹩脚编剧,非要在一个人的人生里埋下两个一模一样的数字,一个用来造梦,一个用来梦碎。对王永红来说,这个数字是3700万。 九十年代末的空气里都躁动着暴富的因子,这个本来拿着经济管理硕士学位的公务员子弟,不仅没回江西宜春过安稳日子,反倒是在北京的洗车铺子里熬了三年。谁也没想到,那一身沾满泡沫的工装底下,藏着后来震惊整个地产圈的野心。 他用一种几乎是赌徒的决绝,把辛苦经营起来的连锁加油站一股脑打包卖给了正在进行行业整合的中石化。那一年,他手里攥着的变现金额恰恰就是3700万。 这一桶金如果是普通人拿着,也就那个时代买几套房收租的剧本,但王永红偏偏不信邪。他看中了朝阳区常营乡一片根本没人瞧得上的荒地。那是实打实的高粱和玉米地,周围荒草连天,除了野狗没人光顾。 拿着全副身家去换600亩没人要的边角料,周围人都觉得这小子大概是疯了,要么就是钱多烧得慌。 但这恰恰是他人生最大的一次侥幸,也是最致命的一剂致幻药。他在那片玉米地里整整蛰伏了八年,赌的就是时代的巨轮会碾压过来。事实证明他押中了,2008年奥运风起,地铁通车,城市版图扩张的红利像海啸一样涌来。 那600亩地摇身一变,成了著名的“北京像素”。凭借着复式设计和4.89米的挑高,加上近万套的庞大体量,这个项目像印钞机一样不仅让他净赚50多个亿,还顺手把他送上了江西首富的宝座。 这种“等风来”的暴利模式,彻底摧毁了他对商业规律的敬畏。当一个人的财富积累速度远超他的认知提升速度时,悲剧的伏笔就已经埋下了。从北京像素尝到甜头后,王永红觉得这世上就没有资本摆不平的事。 他像一只被惯坏了的贪吃蛇,开始疯狂吞噬一切看似光鲜的概念:手游火,就跟风买工作室;电影热,就砸重金搞宣发;旅游地产看着高级,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四处并购。 这种毫无章法的跨界扩张,在2015年的海南半山半岛项目上撞得头破血流。这个3000亩的巨无霸项目成了他的滑铁卢,而在他为了扩张不惜违规填海造地被监管部门当头棒喝时,那张罚单上的数字竟然又是刺眼的3700万。 命运把当年送他上青云的第一桶金数额,原封不动地变成了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催命符。现金流的抽干只是表象,真正的内核是——运气这东西,终究没能撑得起他那无底洞般的欲望。 为了维持那个已经千疮百孔的资本假象,王永红把自己活成了一出荒诞剧的主角。最能讽刺他这种“外强中干”本质的,莫过于那场轰动拍卖界的闹剧。为了博红颜一笑,也为了在名流圈维持那个挥金如土的人设,他竟然在佳士得的拍卖会上,对面那尊雍正粉青双龙尊喊出了1.24亿港元的天价。 那一刻的聚光灯多么耀眼,后来的打脸就有多么清脆。就像他在资本市场上疯狂质押股权换取流动性一样,这个天文数字的叫价背后,是他根本无力支付的一纸空谈。付了定金却付不出尾款,不仅不仅让自己成了被拍卖行起诉的老赖,更在那个关键节点上,把自家资金链断裂的遮羞布当众扯了下来。 这时候的王永红,与其说是个企业家,不如说是个已经被赌红了眼的囚徒。当名下的中弘股份巨亏25亿,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膨胀到800亿这个惊悚量级时,他做出的选择不是力挽狂澜,而是彻头彻尾的背叛。 在中弘股份还没正式成为A股史上第一只因股价低于面值而退市的“仙股”之前,这个幕后操盘手已经通过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违规操作,套走了公司仅剩的61亿救命钱。 这场大溃败的最后甚至剥落了人性的底色。当巨额债务压顶,这位曾经为了追求女明星韩熙庭可以豪掷1.2亿买古董、带着去国外电影节走红毯的风流富豪,却连一张回家的机票都不敢买。当他的老父亲躺在病榻上弥留之际,甚至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也没能等来那个让他引以为傲的儿子。 此时的王永红,正带着巨款和那个女明星躲在香港的豪华公寓里,虽然上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坐不了高铁飞机,但他早已把自己流放到了亲情的荒原之外。 这种靠透支未来和良知换来的苟且,终究是有期限的。2019年,随着王永红的回国自首,这场横跨二十年、从洗车工逆袭到百亿大亨再到阶下囚的黄粱一梦戛然而止。那片曾经长满玉米的土地依然在北京五环外熙熙攘攘,但他早已不再是那个故事的主角。 当年那个在寒风中给人擦轮毂的年轻人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一生中最昂贵的代价,不是那尊没买单的古董花瓶,而是把自己灵魂里的底线,以最低廉的价格在欲望的赌桌上典当一空。 信源:2000年江西小伙在北京五环买下600亩荒地,8年挣50亿如今终落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