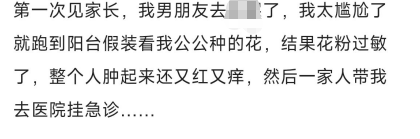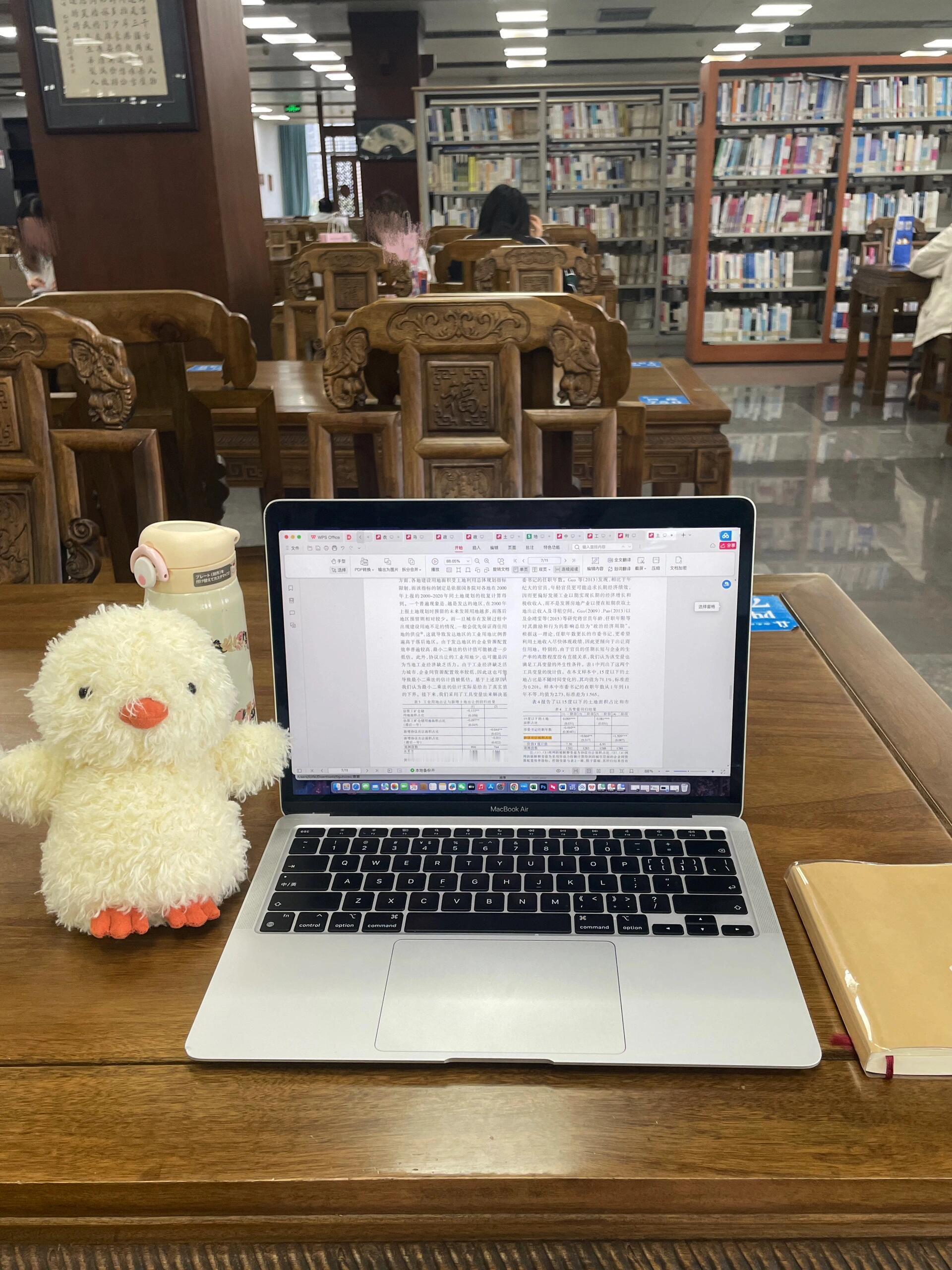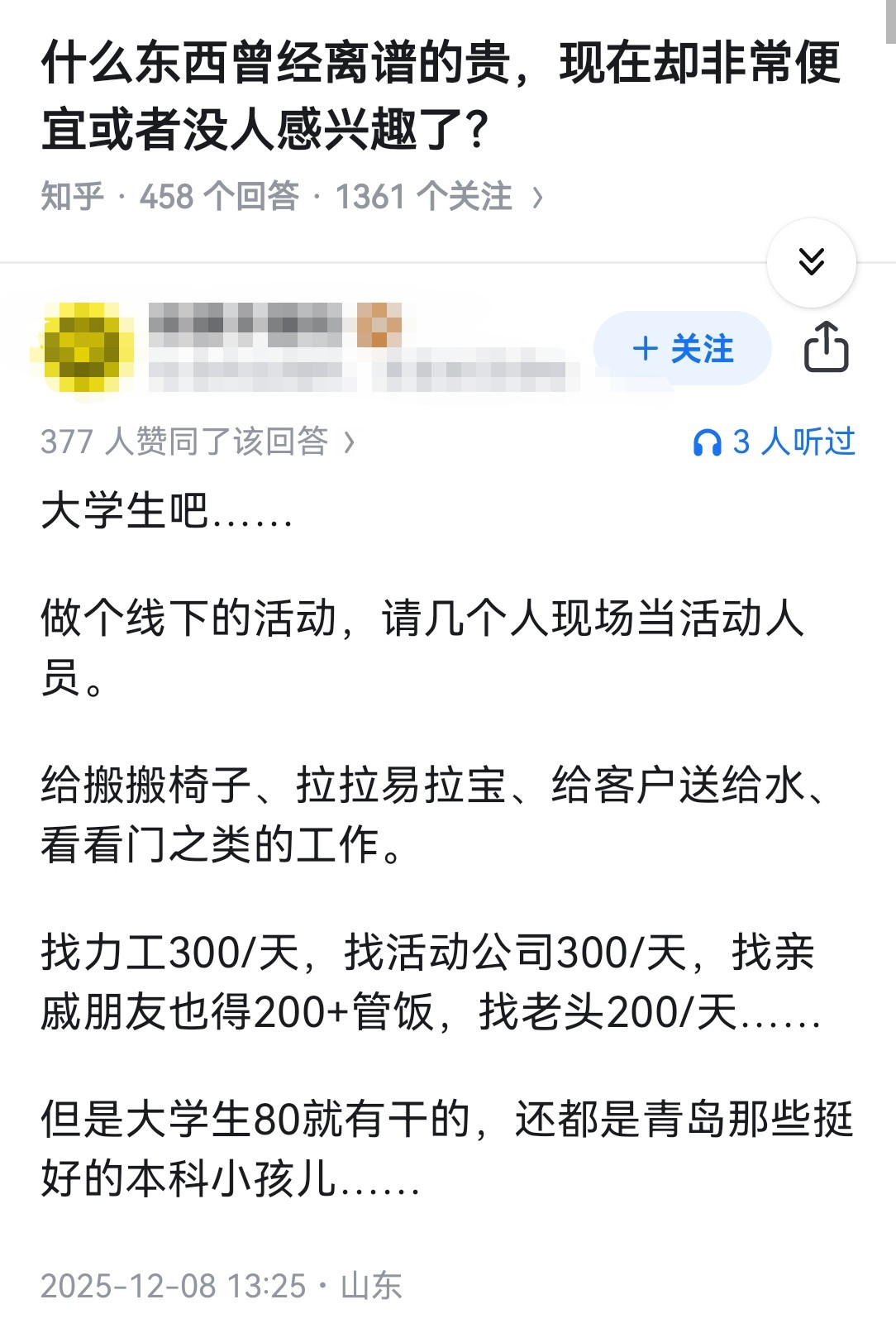按下按钮,没反应。 再按,还是没反应。 万米高空,杨国祥的脑子估计嗡的一下就炸了。底下挂着的,不是演习弹,是咱国家第一颗准备实战的氢弹。 现在,这玩意儿死死粘在飞机上,跟他成了连体婴。 啥概念? 你开着一辆载满炸药的卡车,保险栓还坏了,路上随便一个颠簸,你跟周围几公里就直接从物理上消失了。 他有三个选择: 1. 跳伞。自己活了,但鬼知道这架带着“大宝贝”的飞机会栽到哪儿去,砸出个多大的坑。 2. 找个无人区,连人带机,轰轰烈烈。悲壮,但失败的原因就成了千古之谜,无数人的心血白费。 3. 带弹着陆。把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氢弹,稳稳当当降落到跑道上。这选项,听着就像个疯子的遗言。 他选了3。 没有犹豫太久。因为他脑子里想的,可能根本不是自己的命,而是这颗弹为什么没下去?问题在哪?不搞清楚,下一次怎么办? 那一次返航,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每一次气流的颠簸,都是在跟死神掰手腕。 最后,他成功了。 把一枚氢弹,像捧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轻轻地、稳稳地,放回了地面。 后来查明,是温差导致的电路问题。 一年后,还是他,驾驶着同一架飞机,把改进后的氢弹,扔在了罗布泊。蘑菇云腾空而起。 有些人,你把他扔在任何一个时代,他都是那个能把整个民族的脊梁骨给撑起来的人。 不为别的,就为那份“我得把它带回去”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