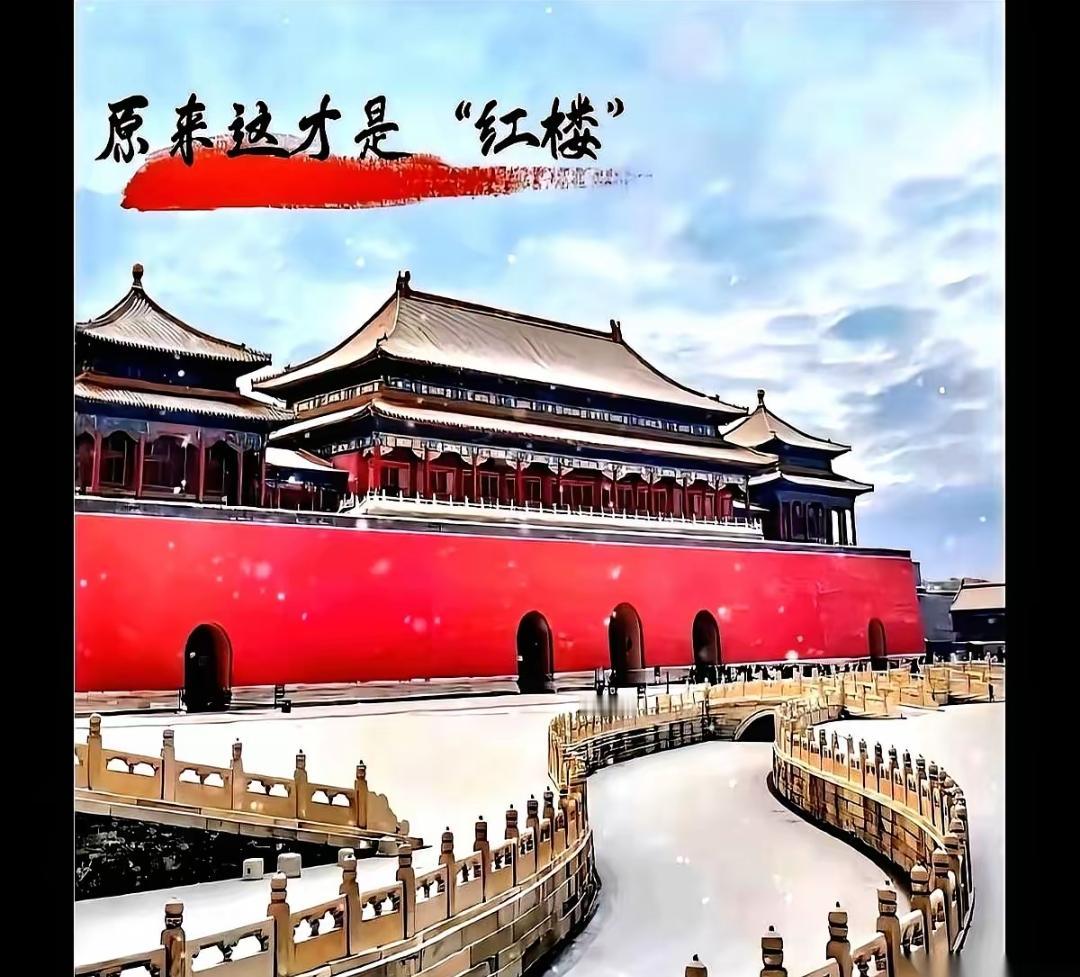兆惠和富德之间矛盾很大…据说是因为兆惠出身于富贵家庭,富德出身于穷苦人家,而富德非常仇富。所以在西北共事的那两年,富德看见兆惠就烦,但兆惠又是他的领导,他也只能忍着。 兆惠这个“天之骄子”,可不是个只会享乐的纨绔子弟。他能被乾隆看重,委以平定西北这个关系国家安危的重任,那是有两把刷子的。 兆惠的厉害,在于他的冷静和战略远见。 一个具体事例: 在乾隆二十一年底,兆惠刚刚上任,就和远在北京的乾隆产生了第一次战略分歧。当时北疆准噶尔降而复叛,但兆惠却敏锐地察觉到,南疆大小和卓才是“燎原之势,后患无穷”。乾隆觉得兆惠小题大做,坚持“先北后南”,要兆惠先解决阿睦尔撒纳。兆惠虽然心里很清楚南疆的威胁更大,但他权衡再三,选择了服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在乾隆这种“面善心狠”的皇帝面前,谁敢轻易挑战? 兆惠在平定北疆后,终于被催着去南疆,这又是一个体现他冷静到近乎冒险的决策。 又一个具体事例: 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兆惠率领不到4000人,直扑小和卓霍集占的老巢——叶尔羌。 “兆惠本来想等一下援军再出发的,可是架不住乾隆数日一封诏书地催,要他立刻南下,赶在年内彻底消灭小和卓。” 兆惠在敌情判断上虽然被霍集斯误导,以为小和卓只有两三千人,但即便是4000对上两三千,长途奔袭、后勤艰难、深入腹地,这仗也绝不好打。更何况,实际的叛军已经超过了两万人。 兆惠为什么不等?他等不了,他知道乾隆“性子很急”,自己已经在北疆耽误了一些时间。他选择用兵贵神速,拿自己的出身和性命,去赌一个“年内结束战争”的承诺。这要的不只是胆量,更要有对胜利的极致渴望和对自身能力的绝对自信。 再看富德,那可是个敢打敢拼的“狠人”。他不像兆惠那样,有大把的时间去思考战略,他更像是冲锋陷阵的“战术大师”。 富德的“忍”和“不服”: 在伊犁善后期间,富德一直是兆惠的副手,是被“酌量调取”给兆惠策应的人。这在官场上,就是“配角”和“听命者”。他看着兆惠这种“关系户”在自己头上指手画脚,心里能痛快吗?肯定有不服气。 这种不服气,结合他“从穷苦人家”拼上来的经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仇富”这种简单粗暴的情绪。但更深层次的,是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 富德: 相信军功至上、能力为王。 兆惠: 既有能力,更有出身背景的加持,更懂得政治上的平衡和妥协。 这种矛盾,在后来的战事中,其实也影响了他们的合作。 一个具体事例: 在兆惠被小和卓霍集占困在叶尔羌,面临“黑水河遇险”时,兆惠立刻派人通知富德从北疆策应。富德虽然在后来千里驰援,横穿“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救了兆惠,但他在调兵、行军的配合上,是不是全力以赴?是不是心甘情愿?这在后世一直是个谜。 “在平定西域的战争中,富德就和兆惠有矛盾。额尔登额是富德的侄女女婿,兆惠和明瑞是一派。同行是冤家嘛。” 从后来的额尔登额“见死不救”明瑞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朝军中的派系斗争多么严重。富德和兆惠,就是这场派系斗争中的两个主角。富德为了自己的阵营,会不会在策应兆惠时“留一手”?这不仅仅是“仇富”,更是复杂的官场博弈。 历史吊诡的地方就在于,将帅不和,却往往能缔造奇迹。兆惠在叶尔羌以寡敌众的困局,最终引出了富德的驰援,以及后来的“黑水营之围”和“富德解围”。 设想一下“黑水河遇险”: 兆惠为了抢夺牧民牲畜,中了小和卓的计。一万四千多叛军火绳枪兵埋伏在桥的另一边,桥下埋好火药。兆惠过桥时, “兆惠正走在桥中间,忽然一个将领指着岸边,惊讶的说道:‘咦,那是什么情况?’…只见远处一缕青烟,正向桥这边飘了过来,他略一迟疑,猛然惊醒,是导火索。于是兆惠大喝一声:’赶快离开桥!’然后纵马向前,冲了过去,刚一下桥,背后就轰然一声巨响,兆惠被气浪从马上掀了下去……” 兆惠大难不死,但陷入困境。这时候,富德的援军就成了兆惠唯一的希望。 富德的“仇富”,兆惠的“不急”,这些都是人性中最真实、最复杂的一面。但把这些复杂的个人情绪放在“平定西域”这个宏大的历史使命面前,它们最终都要让路。 乾隆不是一个只看出身的皇帝,他要的是能办事的人。兆惠、富德,无论他们私底下有多么不和,但在西北的戈壁、沙漠中,他们都拿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和智慧。他们的矛盾,不是历史的主题,如何将叛乱的南疆,重新纳入中国版图,才是主题。 这场由“出身”矛盾引出的西北大戏,最终以大小和卓的覆灭而告终,兆惠和富德,也因此留名青史,成为乾隆盛世的“紫光阁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