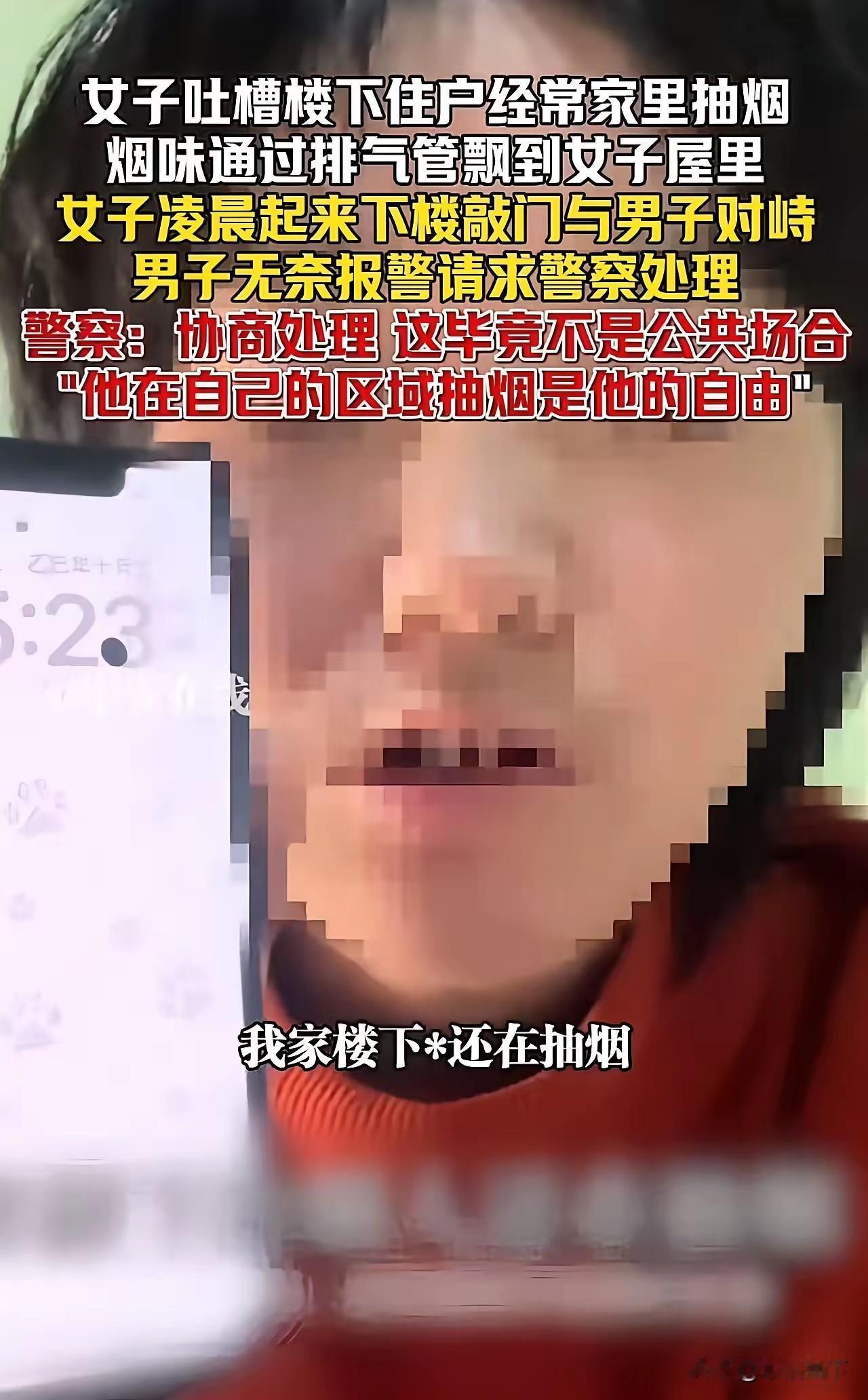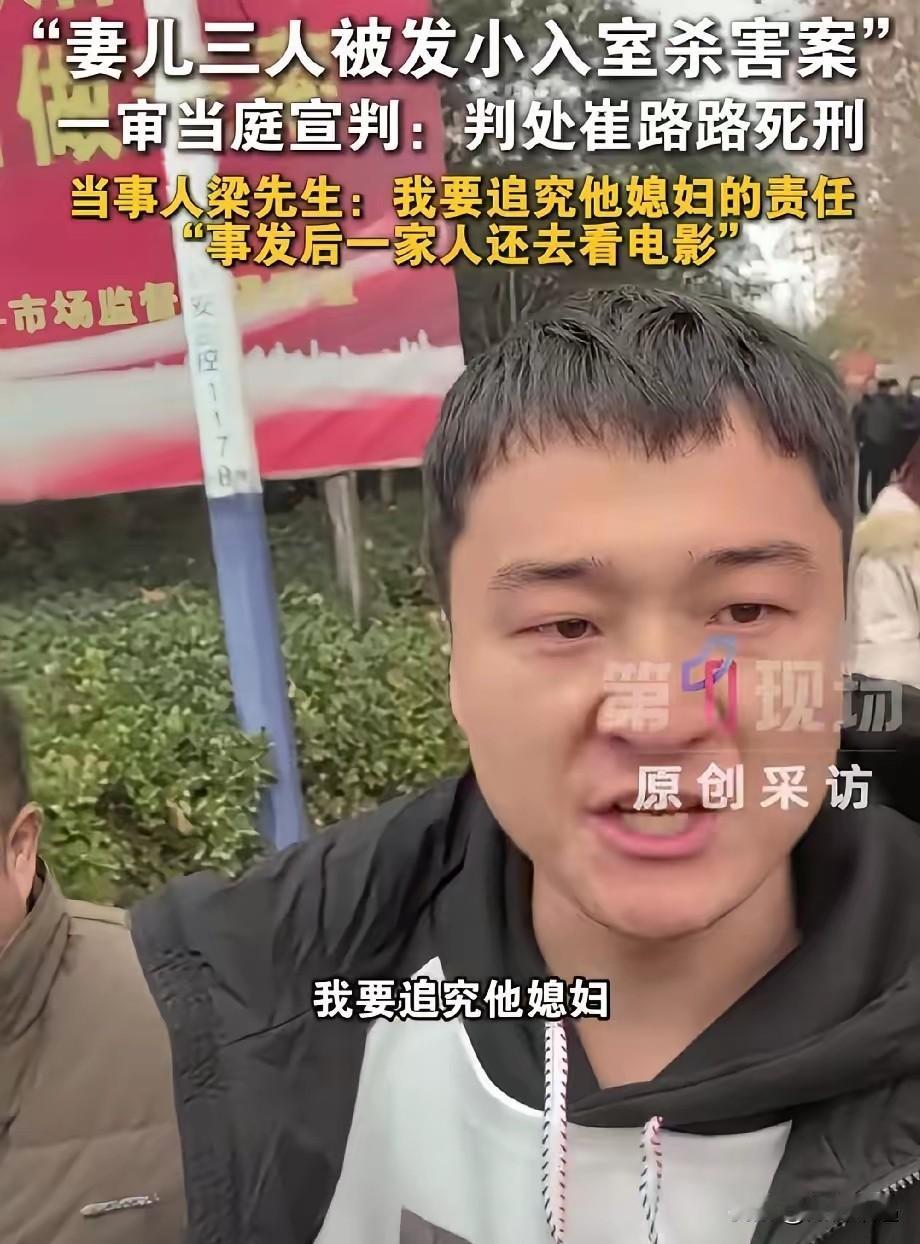头发掉得厉害。 站在楼上往下看,别人家的灯,一盏一盏地亮着。 没人问过我今天吃了什么。 没人关心我打游戏输了几局。 半夜一两点,脑子里一片空白,连个能恨的人都找不到——这感觉比恨更难受。 他们总说,离婚的女人,自由了,解脱了,该为自己活了。 狗屁。 自由是手里攥着选择,不是手里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扇打不开的门。你懂吧?那扇门外面是女儿的笑声,里面是你一个人对着电视屏幕发呆。 视频的时候,你得把摄像头对准天花板,或者对着墙角。 因为你不能让她看见你在哭。你得笑,笑得声音都在抖,还得说妈妈很好,妈妈今天吃了好吃的。 挂了电话,脸是僵的,手心全是汗。 这不是什么“单亲妈妈的伟大”,这就是一道没得选的题:要么让她看见你的狼狈,要么让她相信一个谎言。你选哪个? 我选墙角。 那些劝你“活出自己”的人,从来没告诉过你,“自己”早就被拆碎了。 一部分跟着女儿走了,一部分留在那张离婚协议里,剩下的这点,每天在空房间里飘着,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你看着楼下那些一家三口,不是羡慕,是陌生。就像在看另一个星球的纪录片,你知道那里有温度,但你摸不到。 这不是孤独。 孤独是你还能走出去,还能遇见人。 这是被焊死在了一个透明的罩子里,你看得见全世界,全世界看不见你。 头发一把一把地掉,梳子上缠的都是。 我以前总嫌麻烦,现在倒希望它能多掉点,好像这些头发能替我把心里的什么东西带走似的。 带不走。 压力这东西,不长眼睛,它不认你是男是女,是离婚还是失业,它只管往你最疼的地方钻——钻到你对着镜子,都认不出里面那个人是谁。 说真的,我讨厌那些轻飘飘的“加油”。 加油往哪儿加?油箱早就漏了。 我要的不是加油,我要的是一把扳手,能把焊死我的罩子撬开一道缝,哪怕就一道缝,让我能把手伸出去,够一够我女儿的脸。 就这个念头,撑着我每天睁开眼睛。 没意义也得睁,没盼头也得等。 等什么呢? 等一个可能永远也来不了的“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能挣到足够的钱,什么时候能有间像样的房子,什么时候法律能再看我一眼。 我知道,这些话不阳光,不积极。 但有些真相就是晒不进太阳的,它长在背阴处,潮湿,发霉,可它也是真的。 把它说出来,不是为了让人可怜,是为了让那些同样躲在墙角的人知道:你不止一个。 罩子很厚,但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