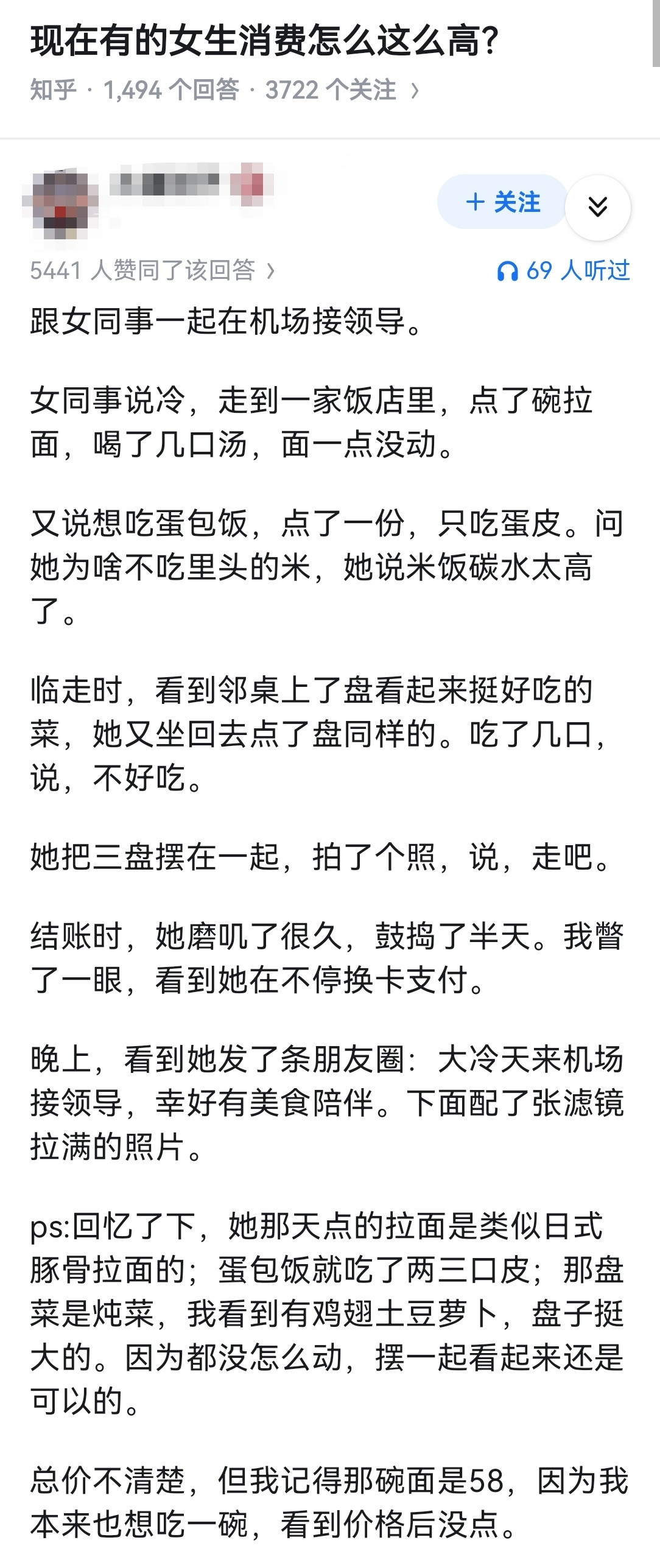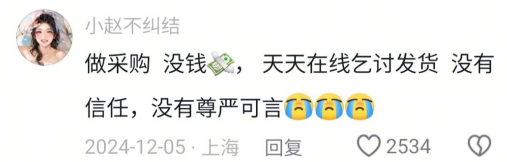1956年,吃下堕胎药的张爱玲,在床上疼的直打滚。突然,孩子掉下来,她长舒一口气说:“终于下来了!”随后将孩子扔进了马桶里! 1956年,纽约的冬天格外阴冷,布朗克斯区的一间出租屋内,暖气片偶尔发出几声干巴巴的敲击声,像是在嘲笑屋里的寒酸。 这一年,三十六岁的张爱玲,正蜷缩在破旧的木床上。她脸色惨白,汗水把鬓角的头发湿成了贴在脸上的黑线,整个人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 其实,她刚吞下了几粒从黑市弄来的堕胎药。 那药装在没标签的小瓶里,是一个犹太女人私下递给她的。在当时的美国,这事不仅风险大,而且不合法。但张爱玲没得选,她手里紧紧拽着床角,指甲缝里都是木头的木屑,疼到深处,她只能死死咬住嘴唇,直到泛出紫红的淤血。 这种疼不是一阵,而是像无数把小钩子在腹部不停地搅动。她不敢大声呻吟,怕惊动邻居,更怕惊动那个同样在隔壁受苦的男人——费迪南赖雅。 很多人想象张爱玲,总觉得她应该是旗袍裹身、烟视媚行的。可真实的情况是,1956年的张爱玲,正处在人生中最落魄的阶段。 她二婚嫁给的美国作家赖雅,比她大了近三十岁。赖雅这时候已经中风好几次,眼睛也快瞎了。两个人住的公寓连暖气都供应不足,冬天全靠一个小电炉取暖,吃饭基本靠廉价的罐头。 说白了,他们两个是两个落魄的灵魂在废墟里抱团取暖。 发现怀孕那天,张爱玲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街道。她对赖雅说:“我们可能要有个孩子了。” 赖雅沉默了很久,久到空气都凝固了,最后他只丢下一句:“你决定吧。” 这句话听着是尊重,其实是逃避。张爱玲心里跟明镜似的:赖雅已经老了、病了,他连自己都养不活,如果再多一个孩子,那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孩子生下来,不是新生命的开始,而是全家人的绝路。 疼痛持续到凌晨,那是人意志最薄弱的时候。 终于,那团尚未成形的小生命滑出了体外。那一瞬间,张爱玲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整个人脱了水,虚脱地趴在卫生间门口。她喃喃自语了一句:“终于下来了。” 这五个字,没有怜悯,只有一种逃出生天的解脱感。 她强撑着站起来,把那团血模糊的东西包好,摇摇晃晃走到马桶边。随着“哗啦”一声响亮的抽水声,那个还没来得及看世界的孩子,消失在纽约幽暗的下水道里。 那一刻,张爱玲不仅仅是扔掉了一个胎块,她似乎也把自己最后一点跟世俗家庭的联系给冲走了。 你可能会觉得她冷酷。但如果你翻看当时的史料,你会发现张爱玲这时候的稿费收入极不稳定。她甚至得精打细算到每一张写稿用的纸。她没钱请医生,没钱买补品,甚至连坐月子的时间都没有。 她必须马上回到那个昏黄的灯泡下,继续写她那些刻薄又清醒的文字,去换明天的罐头。 有人问,张爱玲就不爱孩子吗? 其实,你看她的《小团圆》就知道了。那本书里,她描写过类似的场景,文字极其精准,甚至精准到让人发毛。她说那种疼是“一种古老的酷刑”。她不是不痛,她是太痛了,所以才表现得那么漠然。 张爱玲的这种“冷”,其实是从骨子里带出来的。 她小时候在上海,亲妈为了追求自由常年不在身边,父亲又是个抽鸦片、打骂女儿的旧式男人。她曾被父亲关在黑屋子里半年,差点病死。从小到大,她感受到的家庭温暖极少,她习惯了单打独斗。 对她来说,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她对自己都这么狠,对一个还没成形的孩子,她选择了最理智但也最残忍的处理方式:不让它来到这个苦世受罪。 这件事,张爱玲在往后的信件里几乎从未提及。她照常给朋友写信,聊纽约的物价,聊赖雅的病情,聊她的翻译工作。 她把那晚的血腥和剧痛,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1995年,张爱玲死在洛杉矶的一间公寓里。 她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地板上堆满了旧书和吃剩的塑料盒。她甚至给自己穿上了一件赭红色的旗袍,体面地等待死亡。 回看1956年的那个深夜,如果她留下了那个孩子,结局会不一样吗? 大概率不会。那个年代,一个带着病残丈夫和幼子的异乡女人,文字又是那种清冷小众的风格,生活只会更加破碎。 张爱玲这一生,其实一直在做减法。减掉不忠的胡兰成,减掉拖累的亲戚,最后减掉了这个孩子。 她活得像一柄手术刀,清醒、锋利,切开了生活最难看的脓疮,但也伤到了自己。 我们现在读她的书,感叹她的文笔,其实都只是在看那层“华美的袍”。而那个深夜马桶里的水声,才是她人生里最真实、最沉重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