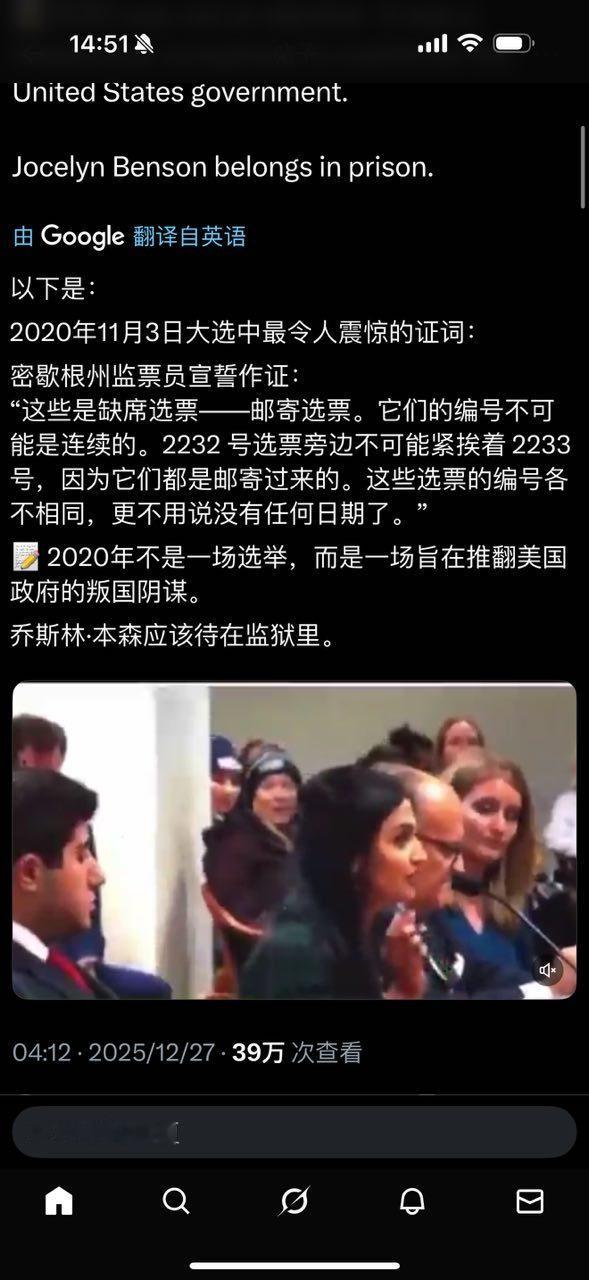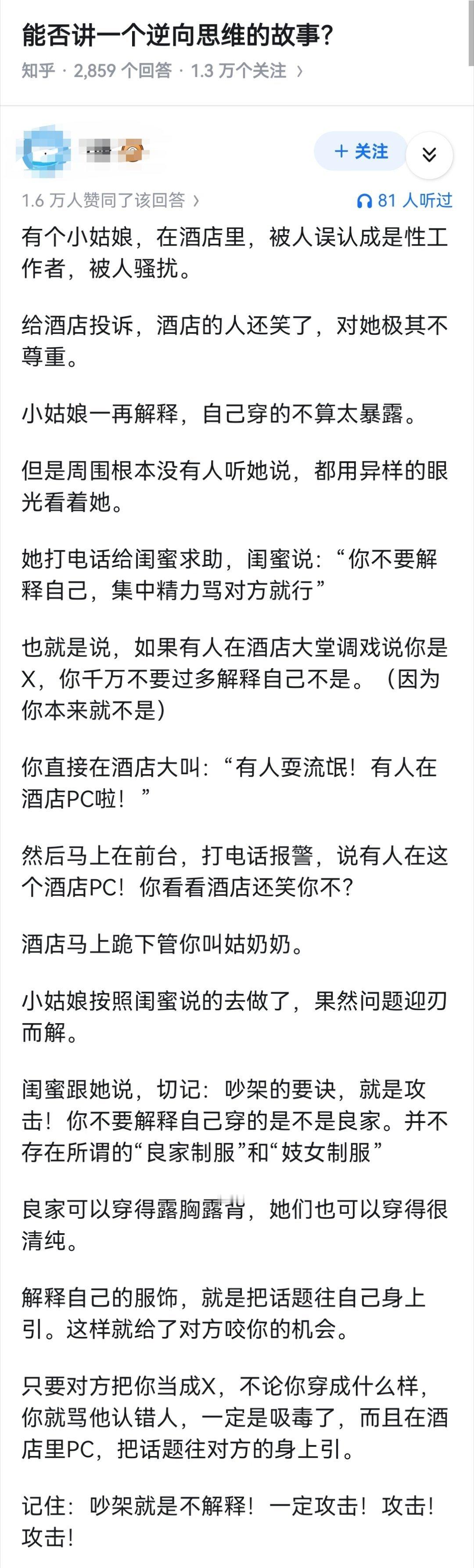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告诉我,崩塌是绝对的,不崩塌是相对的。一年级时,老师告诉我要诚实,放学时老师问全班学生:“你们谁不喜欢打扫卫生?”我诚实地举起了手。老师说:“你留下打扫卫生,别人可以放学了”。刚上学时家里给我买了一个铁制的文具盒,那个文具盒我只用了一天。因为第一天放学时我发现文具盒丢了。第二天我发现同桌用的文具盒跟我的一模一样。说是同桌其实是同排,那时候的桌子是一片木板,长长的木板两头架起,就是一排,一排8个人。后来我自己找到他家里,他姐姐在家,姐姐比我们大上七八岁,在我眼里是大人了。姐姐问他是不是偷了同学的文具盒,他说不是,后来就让我回家了。我没有告诉父母,此后的三十多年,我也再没有用过文具盒。二年级时,老师说被欺负了要告诉老师,后来我就说了一次,也没见那孩子咋样,反正放学后我被揍了一顿。那时候家里养着牛,有一次去放牛,是9月。我家的牛平时还比较听话,那次可能是因为怀孕了,偷吃了一些隔壁田里的玉米,当时也没人看见。回家后那家两口儿来我家问我是不是我家的牛吃了他家的玉米,我说是。然后他们拿着铁锹打牛,锹把都打断了。我的老母亲现在提到这个事情,还是会老泪纵横。母牛分娩是在冬天,下着雪,在我家客厅里生的。三年级时,迎接上级检查,老师说要我们从家里拿工具打扫卫生,我带了一个盆,后来变成学校的了。四年级时,校长说我们要多运动,更要多劳动,身体健康,这样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然后我们被带去校长家的地里刨花生,校长说不许吃,我比较听话,没有吃花生。后来别的同学回家了,我还在地里干到天黑。五年级时,乡里统考,学校之间互相监考,老师说要尽量帮助其他同学,我就把卷子答完后借给别人抄,后来被抓,成绩作废。六年级时,有一次下大雨,早上时天还是黑的。我记得老师说下刀子了也得上学,后来到学校发现就我自己,一个老师也没来。初一时,学校组织捐款,老师说自愿捐款,我就捐了5分钱,这5分钱还是捡来的(那时候没有零花钱一说,也没找家里要)。后来班长一直给我做思想工作,说人家小红捐了5块,别人也没有低于5毛的。我说老师说的自愿。班长说老师交代的最低5毛。我没有捐,自愿就是自愿。后来班长就一直针对我。初二时,家门口的路还是土路,下雨后非常泥泞,偶尔会有过往的农用车陷进去。有一次我刚出门就发现一辆拖拉机上不来了,于是站到泥里给人推车。推上来后,听人家说:“这个傻子还挺有劲儿”。大学实习时,坐火车在我国中部一交通枢纽换乘。晚上11点到,换乘的列车需要等到凌晨5点多发车。我出站时遇见一个腿脚不方便的中年妇女,就帮她拿行李,她问清了我的旅程情况,然后告诉我有一个临时休息的地方,不要钱。去了以后发现是一个非常简陋的旅馆,由一个壮汉带我进屋,妇女随即离开了。屋内一张床和一个暖壶。壮汉跟我要100块钱,我说我不住了,之后他按着我的肩膀,力气很大,一下子就让我坐下来了。然后我交了钱,一会儿离开去候车室了。那时候还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幻想,那些年的火车也很慢,回家的列车多是晚上到达。回我们村还需要坐2趟公交车,所以我会选择在市里的网吧过夜,一晚上5块钱,那时候最便宜的旅馆也要15块钱。去网吧的路上碰见两个农民工,跟我要2块钱买馒头吃,说是包工头欠他们钱不给,现在还跑了,他们实在是没钱了,饿着肚子。我给了他们5块钱,还有包里带的吃的。过了一年,我又看见了他们,跟一年前一样。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也很可怜,我回家后从来不接电话,因为漫游费很贵,一分钟要7毛5。家里给我打电话,我跟他们约定好,我把电话挂了就是没事。但我依然觉得,如果有人因为没有钱而饿肚子了,我要帮助他。我上大学和刚毕业时的工作,都在很远的城市,超过24小时的火车。因为换乘,我在很多地方都休息过,五棵松前面的厕所,几乎没有异味。在北京坐特6公交车去到5环,会有一些正在装修的小旅馆,都是隔板墙,晚上没有人。天桥上有些卖珍珠的、卖玉石的、买首饰的,可能一晚上也卖不出去一件。回忆先到这里,皆是真实,皆是真相。我从来都是一个试图接近规则的人,但在这其中往往是为了迎合某些人。随着这些崩塌,逐渐理解了杨绛的话——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家族聚餐,姑父当众笑我:“挣那点钱不如跟我干。”我低头扒饭没吭声。散场后,他豪车
【2评论】【3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