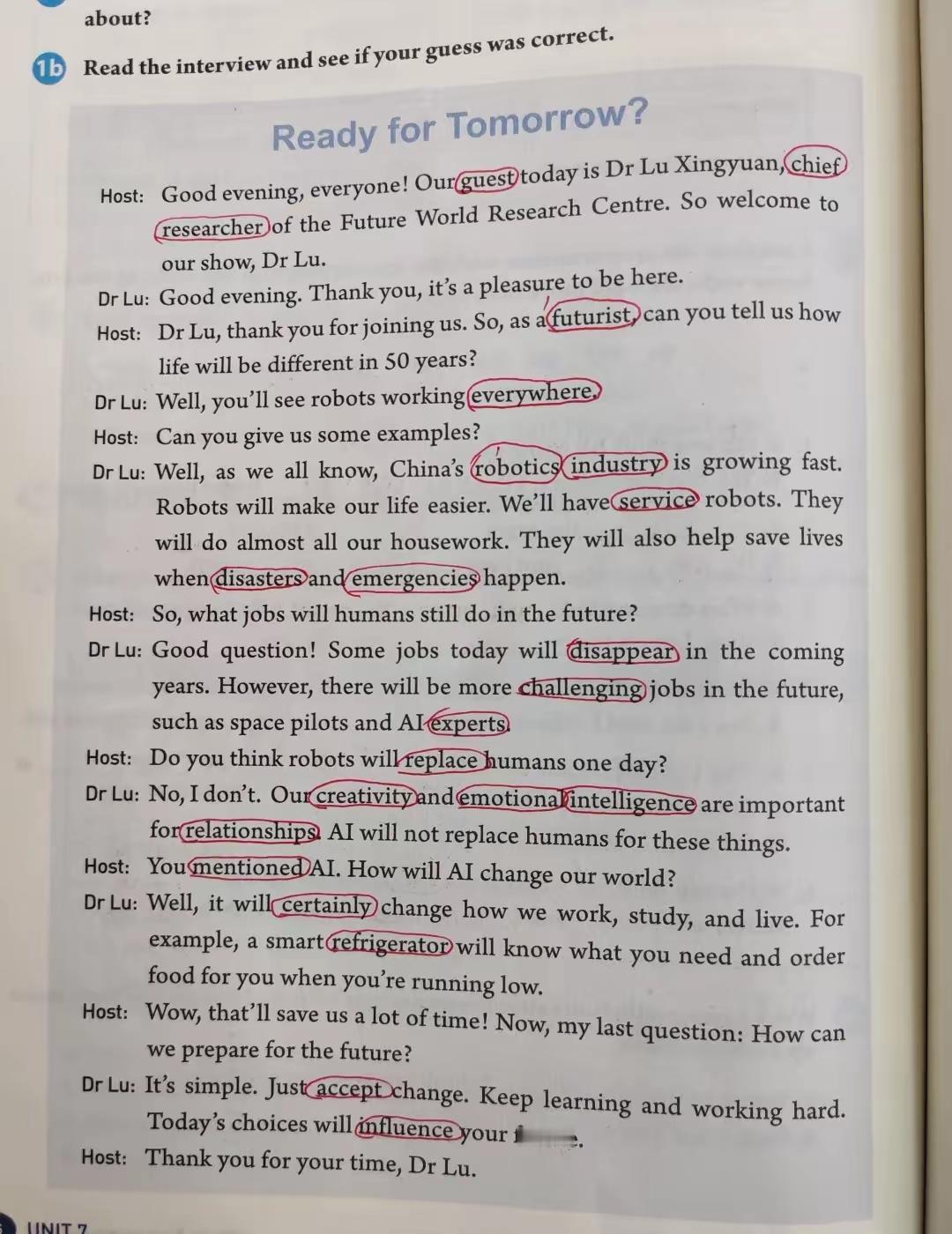1997年,邓亚萍退役后去清华大学读书,第一堂课,老师问她:“你的英语如何?”邓亚萍尴尬的回答:“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 邓亚萍从乒乓球台走向课堂,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重新起跑。1997年,她在二十四岁的黄金年龄选择退役时,手里已经握着十八个世界冠军和四枚奥运金牌,按照许多人的想法,她只要顺势当教练或官员,就能在熟悉的圈子里继续受人追捧。 但她偏偏在这个节点拐了个弯,把自己抛进几乎完全陌生的世界。 让她下定决心转身的不只是伤病,更是对人生边界的思考。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后,她第一次深切感到语言带来的鸿沟。会议上,多数代表可以自如使用英语或法语表达意见,她却只能紧紧跟着翻译,很多想当面讲清楚的观点,难免在转述中打折。 那种有话说不出的无力感,让这位一向在赛场上占据主动的冠军,第一次觉得自己处在被动一侧。 她很快意识到,要在更大的舞台上拥有真正的话语权,光靠球技远远不够,必须把文化短板补齐,尤其是英语。于是,同一年她走进清华园,成为英语系的一名新生。 第一堂课,老师例行询问基础情况,她有些尴尬地说自己连字母表都说不顺,全班一片错愕。摸底考试成绩出来,她的分数稳稳落在末尾,在旁人看来,这个世界冠军好像突然跌回了起跑线的最后一名。 可对习惯了从零起步、靠苦练赢球的她来说,这不过是换了一块场地。她把训练场上的那套节奏照搬到书桌前:早晨五点,清华园还沉在晨雾里,她已经在路灯下背单词;课间、排队打饭时,小声默念的是动词变化;晚上同学结伴出去放松,她常常一个人躲进语音室和机器对话,把拗口的发音一遍遍刻进舌头和耳朵里。 在图书馆,她从最简单的字母和单词开始,咬着牙啃语法和长难句。听力磁带像天书,她就用随身听反复倒带,直到能听出每个音节的起落。 为了把口语练到能应付未来的国际场合,她又自费请英语教练,安排每天对话训练,哪怕一开始说得满嘴别扭也不退缩。四年下来,翻烂的词典、写秃的钢笔、厚厚的笔记本,见证了她从“不会说”到能在课堂上用英语回答问题的全过程。 清华毕业的那一天,她戴着学士帽,用流利的英语作为学生代表发言,掌声把当年那个认不全字母的插班生淹没。 可她并没有把这当作终点,而是把它看作通往更高平台的跳板。很快,她又把目光投向英国,先是在诺丁汉大学攻读与中国当代研究相关的硕士课程,随后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深造土地经济与经济学。 留学期间,她把自己重新变回“书呆子”。图书馆是她第二个宿舍,成堆的英文专著在桌上摞得像小山。遇到复杂的专业术语,她用彩色便签一一点出,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拿去向导师请教。 她用英文写出三万多字的论文,从亲身经历切入,系统梳理中国体育发展的脉络,分析体育产业价值链和改革趋势。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她拿下硕士、博士学位,其中关于中国体育改革的建议,还被国内相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材料。 完成学业回国后,她重新走进国际奥委会和各种国际体育组织的会议现场。此时,她再也不需要翻译“陪同”,可以直接用英语甚至法语与各国代表交锋,把中国体育的经验、理念讲得清楚有力。 里约奥运会筹备期间,她参与协调工作,在会场上切换语言已是家常便饭,许多外国记者对这个能娴熟驾驭多种身份的中国前冠军充满好奇。 回头看她这二十多年的路,从外人眼中的“乒坛女王”到学者、官员,再到在高校讲体育管理、在全民健身活动中做推广的公众人物,她始终在给自己设定新的起点。 她用自己的经历证明,冠军的价值不只写在奖牌上,也体现在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有没有勇气从头学起。 曾经让她挫败的英语,最终成了她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最有力的工具。对于邓亚萍来说,每一次转身都不是真正的告别,而是把人生的球桌搬到更大的世界上,继续打好下一板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