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部队提拔杨国跃当班长,他死活不当。但两年后,在老山战场上,他却抢着当班长,又抢着当排长。同一个人,怎么前后差这么多? 1982年的杨国跃,心里揣着的全是“怕”。他来自川北农村,家里三代都是庄稼人,入伍时刚满18岁,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说话还带着怯生生的乡音。军事训练里,他步枪射击能稳拿优秀,可队列指挥总出错,喊口令时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三排的战友私下里都笑他“闷葫芦”。提拔消息下来那天,他攥着连长递过来的任命书,手心里全是汗,硬是红着脸把纸推了回去:“连长,我不行!” 没人怪他怂。那时候部队处于和平建设期,班长要管训练、管思想、管生活,妥妥的“兵头将尾”。杨国跃见过老班长因为战士内务不达标被通报,见过同乡班长因为带兵方法不当跟战士起冲突,他怕自己没文化,讲不明白道理;怕自己没经验,带不好队伍;更怕万一出了岔子,对不起这身军装,对不起家里盼着他平安的爹娘。他私下找排长交心,说自己就想当个普通战士,把枪练好,到期退伍回家种地,安安稳稳过日子。排长拍着他的肩膀叹气,终究还是尊重了他的选择。 改变发生在1984年春天。老山战役的号角吹响,部队接到参战命令,营区里的氛围一下子变了。往日里的欢声笑语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磨刺刀的寒光、压子弹的脆响,还有深夜里战友们写遗书时压抑的抽泣。杨国跃把家里寄来的照片贴身藏好,照片上爹娘的笑容被他摩挲得发皱。出发前夜,他看到连部的灯亮了一夜,连长正在重新编排战斗班组,花名册上,好几个熟悉的名字后面被打上了星号——那是主动申请留守的炊事员、卫生员,一线战斗班排面临严重减员。 开进老山阵地的路上,他们遭遇了敌军的炮火袭击。杨国跃所在的三班,班长被弹片击中大腿,当场昏迷。没了主心骨,几个年轻战士慌了神,趴在战壕里不敢抬头。炮火声中,杨国跃突然想起班长平时教他的“遇事沉住气”,他咬着牙爬过去,把昏迷的班长拖到安全地带,转身对着战友们吼:“都别慌!跟着我守阵地!”那一声吼,比平时任何一次口令都响亮。 当天晚上,连队召开临时党委会,讨论增补班长。杨国跃第一个站起来:“我来当三班班长!”他的声音还有点沙哑,眼神却异常坚定。有人私下劝他,战场上当班长就是“带头送死”,可他只说了一句:“平时可以当孬种,打仗不能没人扛事!”就任班长的第二天,他带着三班执行侦察任务,在丛林里遭遇敌军小分队。他沉着指挥,利用地形优势交替掩护,不仅成功突围,还缴获了两挺轻机枪。战斗结束后,他的胳膊被树枝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鲜血浸透了军装,他却笑着说:“这点伤,比起牺牲的战友算个啥。” 没过多久,一排长在攻占无名高地的战斗中牺牲,排长位置空缺。这次,杨国跃又抢着报了名。连长看着他布满伤痕的手,问他:“现在不怕了?”他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以前怕的是担不起责任,现在怕的是没人扛责任。战友们把命交给我,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当上排长后,他更拼了。每次冲锋,他都冲在最前面;每次宿营,他都最后一个休息,挨个检查战士的装备和工事。有个刚入伍的新兵怕炮声,他就把新兵拉到自己身边,夜里给新兵讲家里的庄稼地,讲退伍后想办个养猪场,用最朴实的话缓解新兵的恐惧。 有人说,战争最能考验人性。和平时期的杨国跃,想的是个人的安稳,怕的是承担责任;可到了生死攸关的战场,他心里装的全是战友,是家国。他不是突然变得勇敢,而是在炮火中明白了,军装的重量从来都不是荣誉,而是责任。那些曾经让他退缩的“怕”,在“不能让战友白白牺牲”的信念面前,全都变成了“我必须上”的坚定。 老山战役结束后,杨国跃因作战英勇荣立二等功。退伍时,连长送他到营门口,说:“你这小子,和平时期藏着掖着,战场上却比谁都硬气。”杨国跃摸着胸前的军功章,眼圈红了:“以前不懂,总觉得安稳最重要。现在才知道,没有国的安稳,哪有家的安宁。” 如今的杨国跃早已回到农村,守着家里的几亩地,日子过得平淡而踏实。但每当村里的年轻人问起他当年的经历,他总会拿出那枚军功章,反复念叨:“做人呐,该担事的时候就得站出来。和平年代也好,危难时刻也罢,责任这两个字,从来都不能丢。” 时代在变,可“责任”二字的重量从未改变。从和平时期的退缩到战场之上的冲锋,杨国跃的转变,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明明害怕,却依然选择扛起责任。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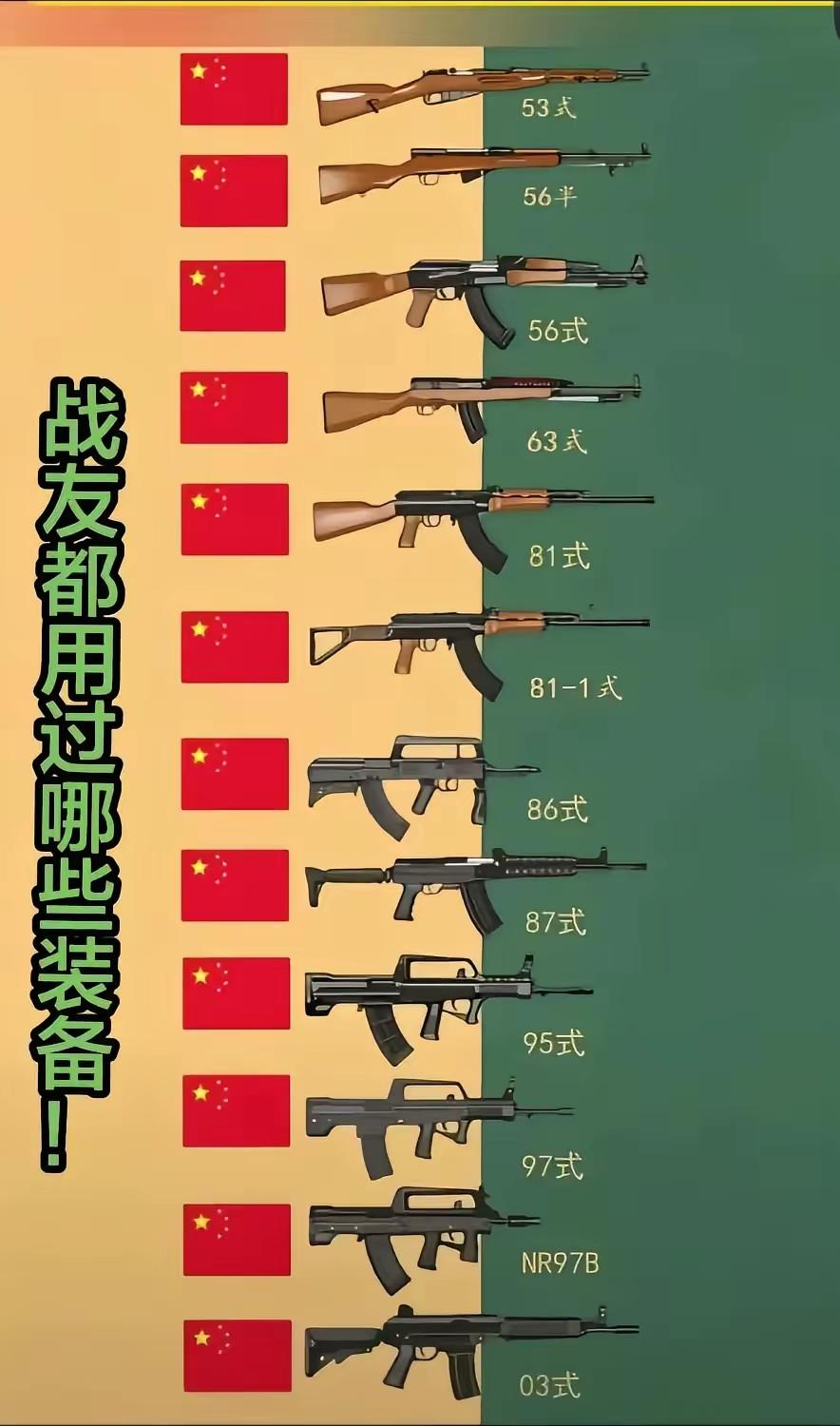

![战场上狙击手就打不了几枪,打一枪就得换个地方[吃瓜]](http://image.uczzd.cn/17447903253540936700.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