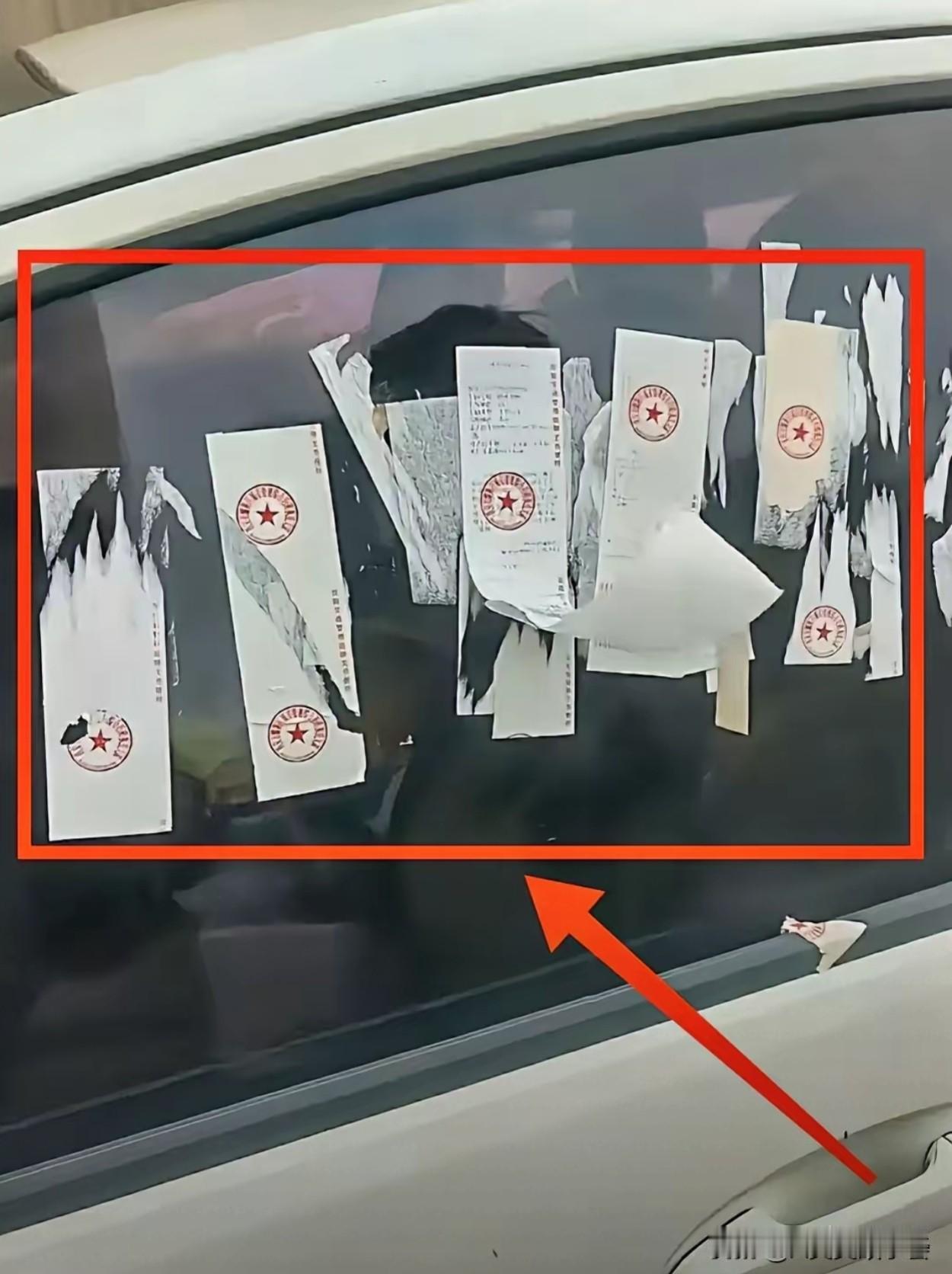一脚油门,车轮原地空转,黄泥甩了半边车窗。 我们几个从西安开车去甘肃庆阳,参加村里哥们的婚礼。他电话里嘱咐:“放心开,下完雪路也清好了,村村通的水泥路!” 结果车开到村口,方向盘都快被我掰断了。 眼前这叫“水泥路”?一条被雪水泡得稀烂的土路,车辙印子深得能陷进去半个轮胎。车身贴着土坡一点点往前蹭,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这场景,不是九十年代初我老家的样子吗? 车窗外,几个小孩穿着厚棉袄,好奇地看着我们这辆挂着外地牌照、满身是泥的铁家伙。旁边光秃秃的杨树枝上,还挂着没化完的残雪。 哥们站在村口,看到我们,一路小跑过来,脸上挂着笑,但眼神里全是过意不去。 他上来就给我们递烟,一个劲儿地说:“委屈兄弟们了,委屈了。” 我把车熄了火,手还在方向盘上搭着,半天没说话。我只是在想,我们是不是跑得太快了,快到把一些地方,连同他们的路,都忘在身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