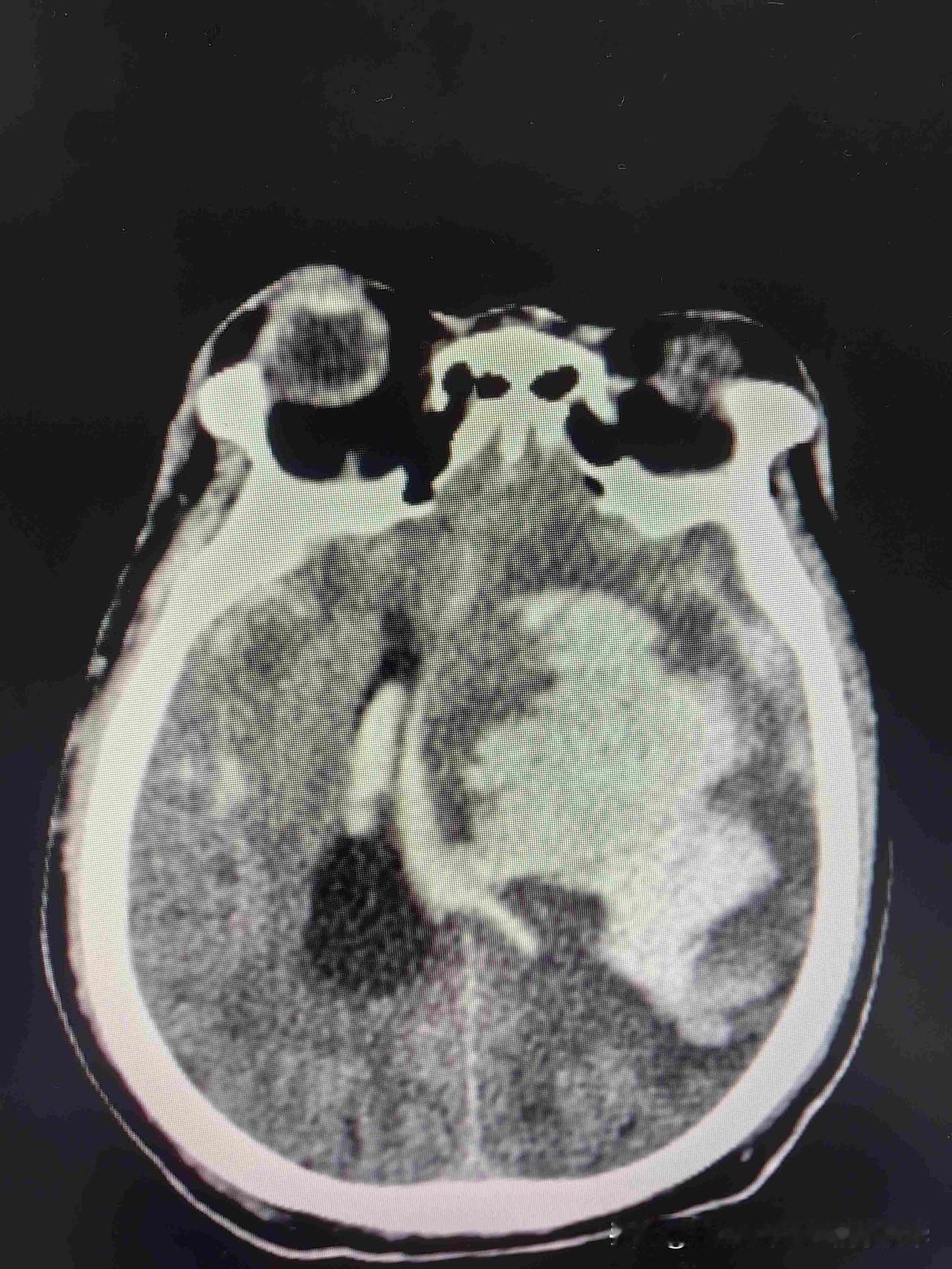1977年,知青于文娟返城,恋人跟着列车狂奔,她抹着泪,大喊道:“别追了,我们不会再见面了!”谁知,于文娟到家后却被母亲撵出家门。 她蹲在巷口的墙根下,行李散在脚边,从陕北带回来的课本掉了一地,封皮上还沾着黄土地的尘。手里攥着那个王建军缝的碎花钱包,指腹蹭过磨毛的布边,眼泪砸在土里,砸出一个个小小的湿印。巷子里的穿堂风一过,地上的书页哗啦啦地响。 正蹲着发呆呢,巷子深处那扇总关着的黑漆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穿着洗得发白旧军装、头发花白的男人探出身,看了她一会儿,招招手:“闺女,进来。” 于文娟愣着没动。男人走过来,弯腰帮她捡起地上的书,拍了拍土,动作很慢。“我姓陈,以前也在陕北插过队。”他声音沙沙的,“这儿就我一人,空房多。进来喝口水,总比蹲这儿强。” 老陈的房子又旧又暗,但收拾得极整齐。他让于文娟住在靠南的小间,窗台上摆着盆半死不活的绿萝。他没多问什么,只说:“先住下,别的慢慢想。”白天,老陈去街道的图书馆当管理员,于文娟就出去找临时工。晚上回来,常看见老陈就着那盏旧台灯,在纸上写写画画。 有一天于文娟回来得早,看见老陈桌上摊着本厚厚的《高等数学》,边上草稿纸密密码码。她吃了一惊。老陈有点不好意思,推推眼镜:“瞎琢磨。以前那点底子,都快忘光了。”他顿了顿,看向于文娟那摞从陕北带回来的课本,“你想考大学,是不是?” 于文娟鼻子一酸,点了点头。老陈把台灯往她那边挪了挪:“那正好。我帮你看看功课,也算……温故知新。”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那盏灯都亮到很晚。老陈讲题极有耐心,讲到函数曲线,会用手在空中比划出山的轮廓。“这就像咱陕北的塬,”他说,“看着陡,找对路,就能上去。”他指甲缝里总有洗不掉的墨迹,茶杯积着厚厚的茶垢。 报名截止前那天,老陈把一张盖好章的介绍信和报名费塞给她。“去报上,”他说,“别的别想。” 考试结束那天,于文娟觉得考得不错,想告诉老陈。她买了条鱼,想着做顿饭。可推开院门,院子里静悄悄的。老陈的屋门虚掩着,人不在,桌上压着张字条,字迹工整:“我回老家看看。你好好上学。橱里有粮票,桌下有给你的书。勿念。” 她打开桌下的旧木箱,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她的课本,每一本里都夹着细长的纸条,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注解和重点。最上面那本《地理》的扉页上,写着一行小字:“山高有行路,水深有渡舟。” 于文娟抱着那箱书,在渐渐暗下来的屋里坐了很久。窗台上那盆绿萝,不知何时抽出了一枝鲜嫩的新芽。
还有治疗的价值吗?前天晚上,张大哥照例跟朋友打牌,打到很晚,走的时候还笑着喊
【2评论】【2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