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要给彭德怀做太师椅,到底犯了什么错误?20年之后才平反 “1959年8月11日,北京西山,一句低声的抱怨传进耳朵——‘让我揭发彭老总?我说不出口。’”说话的人是吴信泉,时年四十八岁,肩扛中将军衔,个子不高,脾气倔强。 吴信泉是湖南平江人。少年时代就跟着彭德怀在平江起义里打硬仗,后来进入红三军团。长征到达陕北时,他还只是个营长,但因为敢冲锋、爱琢磨,被老战士戏称“拼命三郎”。抗战爆发后,他调到黄克诚手下,辗转华北、苏北,最后一同挺进东北。辽沈战役里,第39军强渡大凌河,东北野战军授予他“促成锦州胜利”嘉奖。 1950年10月,第39军成为第一批跨过鸭绿江的部队。临行前,他拍着胸口嚷道:“不只摸老虎屁股,还要把皮扒下来,给彭老总做太师椅!”一句大话在前线官兵里炸开锅,却精准地刻下了他敢说敢干的性格。拿下三所里高地后,他圆了“摸屁股”的夙愿,也伤透了美军的面子。1955年授衔,吴信泉顺理成章地戴上了中将肩章。 1957年,他被调入高等军事学院深造,按说是歇口气的机会。偏偏一年后学院组织“大跃进”参观团,他在河北看密植小麦,皱着眉头问随行干部:“这么挤,风都进不去,庄稼能活?”随口又补了一句,“真要照顾它,还得电扇加灯光,这不是折腾吗?”这话惹得负责人脸色铁青。当时没追究,可不喜欢的印象已经留档。 转折点出现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结束不久,学院接到军委扩大会议通知:列席人员中必有吴信泉。原因很直接——他是彭德怀、黄克诚的老部下,圈里人觉得他“材料多”。会场内外气氛紧张,诸多发言上纲上线。吴信泉听得脸发热,却始终沉默。有人悄悄劝他:“随大流几句,省事。”他只是摇头。 军事学院批判会接踵而至。按照程序,人人要发言,他再逃不过。轮到他时,他只说:“彭总在军事上有过失误,但我没看见他反党。”不足两百字,便合上纸。会后,一位同班少将拍桌子斥责:“你这是对抗组织。”吴信泉回了一句:“我说不出别的话。”语气平静,态度却倔得很。 1960年1月25日,学院政治部向总政治部递交报告,给他扣了“右倾机会主义性质错误”的帽子。处理意见相对含蓄,保留职务,不处分。原因也简单:炮兵系统正缺熟手,吴信泉的业务摆在那里。8月,他被任命为炮兵副司令员。职位在,可帽子也在。 1966年风浪一起,“右倾”三字被无限放大。有人翻出他当年“太师椅”的豪言,说这人骨子里崇拜个人,岛津且反党。批斗会上他被剃阴阳头,脖子挂木牌,胳膊被反拧得青紫。管教对他喊:“认不认错?”他咬着牙道:“错在我说真话,多余。”白天挨斗,夜里关在一个堆满炮闩的仓库,蚊子乱飞。那段时间,他最常念叨一句:“军人不说假话。”话音低,却不改。 身心折磨外,加上家人被牵连,吴信泉的胃病越发严重。1970年冬,他差点因为穿孔送命。医务室里,他对来探望的老副官一笑:“命硬,还没到头。” 1978年春,黄克诚复出,担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吴信泉得知后写了份陈述,迟迟没递。直到1980年3月,他拄着拐杖上门,向黄克诚汇报。黄克诚问:“老吴,还有气没?”他答:“气在,劲也还在,就是帽子该摘了。”黄克诚点头:“该办的,会办。” 同年11月,中央军委纪委下发文件,认定1960年结论失实,吴信泉的问题予以全部平反。文件送到家时,他刚把茶杯放下,扶着桌子站起,连说三声“好”,眼角却湿了。第二天,老将军到总装备部向年轻军官讲炮兵现代化,仍旧嗓门洪亮,只是不再提“帽子”二字。 1992年2月3日清晨,吴信泉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一岁。整理遗物时,人们在抽屉里发现那份发黄的《黄克诚同志给我的教育》原稿。扉页贴着一条旧胶带,上面写着——“事实不会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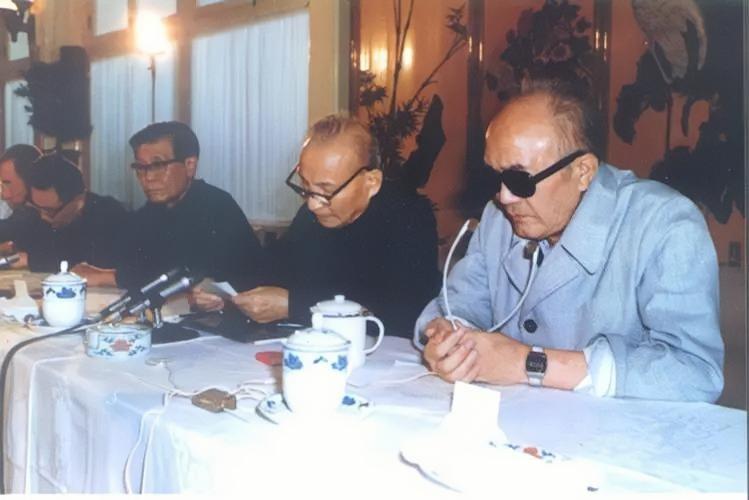



风雨兼程
[赞][赞][赞]
千里草
将军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