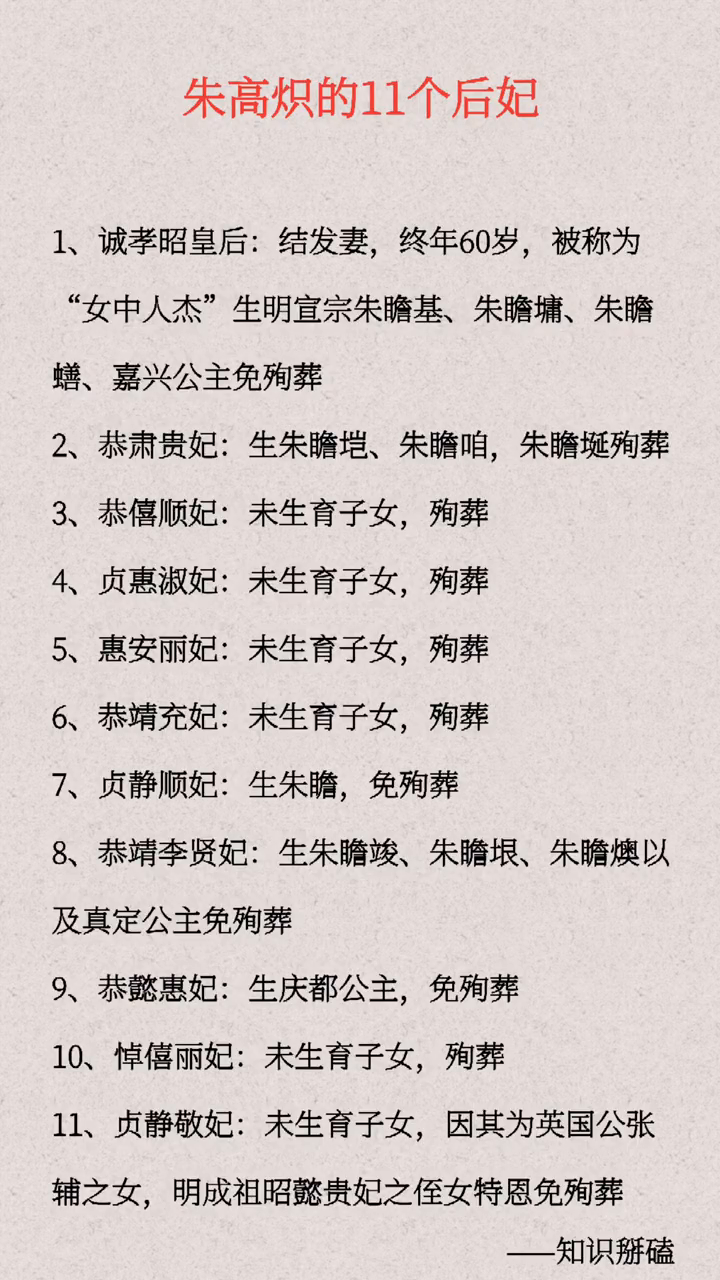450年7月的北魏都城,一辆污秽不堪的木笼囚车中关押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他本是皇帝拓跋焘倚重的 “张良”,此刻却被剥去官服,昔日的宰相威仪荡然无存。押解的士兵一路嬉闹,轮番向囚车中的老人身上撒尿。 这位在七十岁高龄遭受奇耻大辱的老者,正是北魏三朝元老、司徒崔浩。 崔浩出身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 清河崔氏,崔浩的祖父崔潜曾在西晋为官,父亲崔宏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期的开国功臣,官至天部大人,掌管朝廷礼仪制度。 生于这样的簪缨世家,崔浩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天赋。 在那个纸张稀缺、书籍珍贵的年代,崔浩凭借家族藏书与过目不忘的记忆力,积累了渊博的学识。 北魏道武帝天兴年间,二十岁的崔浩进入仕途,担任著作郎一职。这个负责记录国史、编纂文献的职位,恰好发挥了他博闻强记的特长。但真正让他崭露头角的,是在明元帝拓跋嗣时期。 当时北魏与南朝刘宋在黄河流域展开激烈争夺,崔浩以精准的局势分析多次劝谏皇帝,避免了无谓的军事消耗。 崔浩曾力排众议,劝阻明元帝迁都邺城的计划,指出鲜卑贵族不宜过早脱离草原根基,否则会引发危机。 公元423年,拓跋焘即位,是为北魏太武帝。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皇帝渴望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急需有识之士辅佐。 崔浩凭借深厚的谋略素养,很快成为拓跋焘极为倚重的谋臣。 在拓跋焘平定北方的战争中,崔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公元 426 年,北魏准备讨伐割据关中的赫连夏政权,朝臣大多反对,认为劳师远征风险太大。 崔浩精准分析了赫连夏内部的矛盾,指出其主力分散、防备空虚的弱点,力主出兵。拓跋焘采纳其建议,亲率大军突袭夏都统万城,果然大获全胜。 公元429年,北魏与北方强敌柔然的决战前夕,又是崔浩驳斥了鲜卑贵族的畏战情绪,详细阐述柔然的作战特点与应对之策,坚定了拓跋焘北伐的决心。 最终北魏军队大破柔然,俘获人畜数百万,解除了北方边境的威胁。 除了军事谋略,崔浩在政治改革上也颇有建树。拓跋焘对他的信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甚至允许他出入宫廷禁地,参与最高决策。 崔浩的权势与士大夫的身份,始终让鲜卑贵族对他心存忌惮。随着地位日益巩固,崔浩开始着手一项他认为意义重大的文化工程, 编纂北魏国史。他希望通过这部史书,记录北魏从部落联盟到王朝帝国的发展历程。 拓跋焘对此表示支持,下诏命崔浩主持修史,要求 “务从实录”。 崔浩组织了高允等一批文人,开始大规模编纂《国记》。这部史书详细记载了拓跋氏的早期历史,包括其部落时代的习俗、传说以及历代首领的事迹。 按照崔浩的想法,修史应当秉笔直书,即使是皇室不愿提及的往事,也应如实记录。他认为这是 “彰直笔,存真史” 的史学传统,却忽略了鲜卑贵族对自身早期历史的敏感态度。 更致命的是,崔浩做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决定。他在完成《国记》编纂后,认为这部史书应当让世人知晓北魏的 “光荣历史”,于是奏请拓跋焘批准,将《国记》刻在石碑上,立在平城郊外的祭天场所天坛东侧,并修建了石屋保护。 这些石碑上的文字,详细记录了北魏历代帝王的事迹。 石碑树立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鲜卑贵族们看到石碑上记录的先祖往事,尤其是那些涉及部落争斗、婚嫁习俗的内容,认为崔浩是在故意揭露拓跋氏的 “丑事”,羞辱皇室祖先。他们群情激愤,纷纷向拓跋焘告状,指控崔浩 “暴扬国恶”。 拓跋焘起初并未在意,但在鲜卑贵族的持续煽动下,逐渐被激怒。他认为崔浩作为大臣,竟敢公开贬低鲜卑皇室的历史,是对皇权的严重挑战。 暴怒的拓跋焘,下令将崔浩逮捕入狱,同时牵连了崔氏家族以及与崔浩关系密切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汉族世家。 拓跋焘在震怒中下令将这些家族满门抄斩,史称 “国史之狱”。 崔浩被捕后,曾经对他言听计从的拓跋焘拒绝再见他。这位七十岁的老人在狱中或许才真正明白,自己坚持的 “直笔修史” 原则,在鲜卑皇室眼中竟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拓跋焘一生辅佐三位北魏皇帝,为北魏统一北方立下汗马功劳,却其实并没有被拓跋焘当成“自己人”。 在狱中的最后日子里,崔浩承受着身心的双重折磨。他或许会想起年轻时在朝堂上与鲜卑贵族的辩论,想起拓跋焘曾经给予的无上信任,想起自己推动改革的雄心壮志。但现实却是冰冷的,曾经的荣耀都已化为泡影。 450年7月,崔浩被处斩,平城百姓纷纷涌上街头,目睹这位名相的悲惨结局。木笼囚车中的崔浩,在士兵的羞辱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古代建城,红圈中是什么建筑?[并不简单]](http://image.uczzd.cn/142347392438671528.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