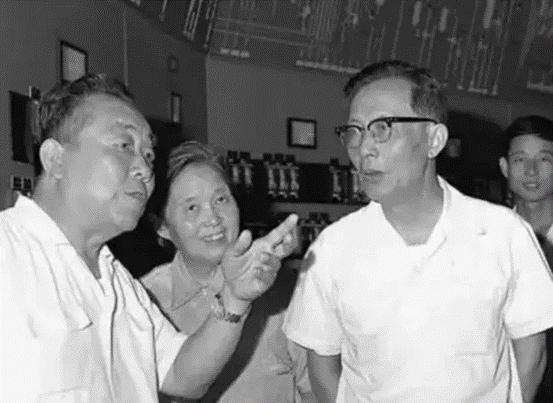他曾一人肩挑安徽省委书记、省长双职,后官至副国级,享年101岁 “1980年3月的合肥,你们安徽缺的不是口号,而是明天的粮和种子。”会议室里,张劲夫语速不快,却让在座干部感觉到紧绷的空气。大雪刚化,春耕在即,谁也等不起。 很多人提起张劲夫,总爱从“财经专家”或“科学院后勤部长”说起,忽略了他其实是从硝烟里爬出来的“才子政委”。1914年6月,他出生在肥东一个普通农家,木质的门框常年被风沙磨得发白。乡亲们只记得,这孩子小小年纪背着旧书箱,来回赶二十多里去上学,脚底打了厚茧。 20岁那年,他到南京晓庄学院,遇见陶行知。陶先生拍着他的肩说:“读书是为了改造社会”,这句话像钉子一样钉在他的脑子里。1935年12月,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不到三年,他已是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政委,一支笔,一杆枪,两样都使得行云流水。战友私下给他取了个外号——“会写诗的参谋长”。 抗战结束后,他没留在军队,而是被抽调到财经口。原因很简单:中央缺能看懂账本、又能带队伍的人。1950年前后,他忙着制定全国财政预、决算,白天和各省代表掰手指数粮票,晚上抱着算盘把数字拨得啪啪响,邻屋以为有人练京剧锣鼓。 1958年夏,他刚在北海办完一场预算会,就被告知去中科院“打前站”。科学家们怕外行指挥内行,对新任党组书记多少有抵触。他进门第一句话却是:“各位,我来给大家当勤务兵。”气氛一下松了。接下来,他拉着几百名专家一起编写十二年科技规划,字字推敲,连标点都抠。 中科院三年,他把“尊重”两个字写得透彻。化学所的老院士说:“张书记批文件从不一挥而就,他总会追问‘这数据怎么来的’。”其实他并非求全责备,而是想让科研经费花在刀刃上。倘若材料报销单上多出几支铅笔,他都会打电话确认——既替国家抠,也为实验室省。 1975年,他重回财政部,手里那本黑皮账册卷角磨得像老农的锄把。正当外界以为他会在部里干到退休时,组织突然决定:驰援安徽。“家乡发大水,谁顶得住就去。”此刻他66岁,却没犹豫。 抵达合肥后,第一件事不是开欢迎会,而是乘吉普车往淮河边走。沿途残垣断壁,孩子们赤脚追着车扬起尘土。一位老人攥住他的手臂:“书记,麦子发霉,化肥也没钱买。”他只回了三个字:“我记下。”当晚他给北京挂电话,财政部很快批下三千万元救灾款。数字不算小,可他仍说“只能解一时急,不能当长久药”。 同年夏,他走遍全省二十多个县。每到一地,只提两个要求:不封路、不开小灶。一次在肥东调研,司机刚伸手去开空调,他摇头:“十几公里,忍一忍。”车到县城,他咬下一块西瓜就和乡亲聊庄稼,临走掏出一元二角压在碟子底下——这是西瓜钱,有人想推回来,被他瞪了一眼,只好收下。 他还不忘老规矩:自带毛巾肥皂。定远招待所怕怠慢大领导,特意搬来木盆让他房里洗澡,他却笑道:“抗战那阵子,我都在河里泡,今天下乡也该和大家一样。”当晚他扛着盆走到公共浴室,年轻干部一脸尴尬,他摆摆手:“别客气,热水别浪费。” 1982年春,他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副国级。听证书念完,他仍埋头在文件上划红线。有人问:“张老,升职了,换辆车吧?”他挥手:“这辆吉普没坏。”后来那部北京212开了近二十年,发动机轰鸣声像老朋友的嗓音。 1992年之后,他主动淡出一线。中央请他出任中顾委常务委员,他答应,但要求“少开会,多调研”。每到地方,他仍自行买车票——虽然工作人员早已把专机安排妥当。有人打趣:“您老人家是真把自己当普通党员。”他只笑:“规矩不能光挂嘴边,总得有人做给后辈看。” 2015年7月31日清晨,101岁的张劲夫在京城寓所安静离世。书桌上那本翻旧的《淮河治理资料汇编》仍摊着,页角夹了几张便签,密密麻麻写着数字。有位老同事站在门口嘴唇发颤:“劲夫走了,可他还欠自己一个休息。” 安徽合肥雨后的晚风穿过街巷,吹在当年他走过的淮河大堤。有人低声说:“这河里的水,新中国建国后改过三次名字,可在老书记眼里,它始终叫‘老百姓的命根子’。”话音落下,河面泛起涟漪,像是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