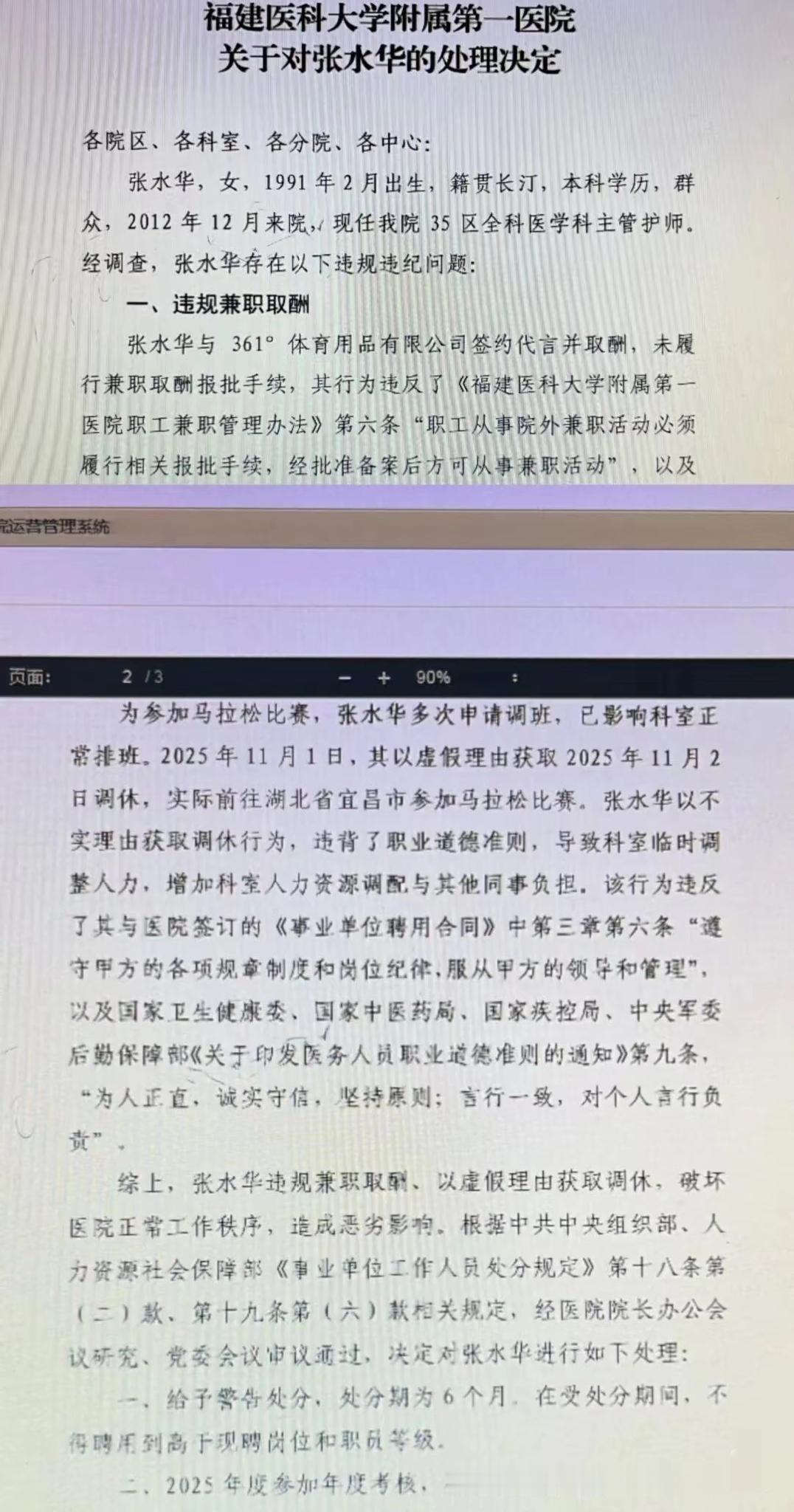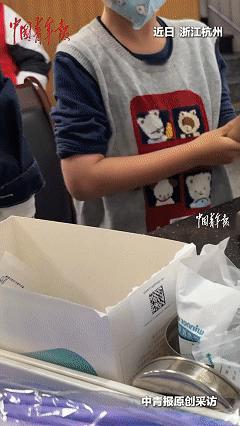1982年6月16日,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结果震惊发现,他全身都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47岁,正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最能出成果的年纪,在场所有人都红了眼——他们知道,这个把命都耗在实验室里的人,刚为中国捅破了一道技术天险。 可能你从没听过罗健夫,但你今天用的手机、家里的电脑,甚至国家的导弹火箭,里面都装着集成电路。这东西就像电子设备的“大脑”,而要造这“大脑”,首先得有“刻刀”——图形发生器。 没有它,就没法在芯片上刻出复杂的电路纹路,芯片就是块没用的硅片。上世纪七十年代,这设备被国外死死攥在手里,不仅不卖,连图纸都不肯露半个字,咱们国家的微电子产业只能在黑暗里摸路。 1969年,34岁的罗健夫接下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成了图形发生器课题组的组长。我翻到当年同事的回忆,说那时实验室里连台像样的样机都没有,唯一的参考是几张模糊的国外产品照片。 罗健夫本是学核物理的,搞电子设备纯属跨界,更难的是,他学的是俄语,可所有前沿资料全是英语,只能抱着词典一个词一个词啃。有次同事半夜路过实验室,看见他趴在桌上睡着了,脸还贴着英语资料,手里攥着的笔在纸上画满了电路草图。 那些年里,他就像个连轴转的陀螺。调试设备最紧张的两个月,平均每天只睡四个小时,饿了就啃口干馍就咸菜,困了就在塑料板上躺一会儿。 1972年春节刚过,实验室的机器突然出了故障,为了赶进度,他带着团队在零下几度的车间里泡了三天三夜,手指冻得肿成胡萝卜,还是靠着哈气取暖继续焊接线路。就是这样硬拼,当年就造出了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把国外对我们的技术封锁撕开了一道口子。 这台“大家伙”看着不起眼,却比国外同类设备还厉害。之前咱们造芯片靠人工手绘版图,一块中等规模的电路要画半年,稍有偏差就全白费。 罗健夫的图形发生器能用计算机程序控制,把制版时间缩短到几天,而且精度达到1.5微米,畸变量比国外设备还低一半。 1975年他升级的Ⅱ型设备,直接拿到了全国科学大会奖,要知道那可是改革开放后首次全国性的科技盛典,含金量堪比现在的国家最高科技奖。 可很少有人知道,拿奖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团队最后一位。1977年单位调工资,他主动让给了家里更困难的同事,要知道当时他夫妻工资加起来才130元,要养老人和两个孩子,还得贴补患癌的弟弟。 1978年单位要提拔他当研究室主任,他一口回绝:“我搞技术比当领导管用,让我多为国家做点实事。” 1981年,Ⅲ型图形发生器研发到关键阶段,罗健夫的胸口开始疼得直不起身。他瞒着所有人,白天一手顶着胸口一手操作机器,晚上一边熬中药一边查资料,硬挺了三个多月。到北京调试时疼得晕倒,被送进医院才查出是淋巴癌晚期。 同事去看他,本不忍心提工作,他却主动拿出图纸,忍着剧痛讲了两个多小时,从设计逻辑到调试技巧,生怕漏了一个细节。医生劝他用镇痛剂,他摇头:“这药伤脑子,我还得想技术问题,给同志们当参谋。” 他走后,同事们整理他的遗物,除了一堆图纸和资料,只有一件打补丁的衬衣和半瓶没吃完的咸菜。可他留下的图形发生器,却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微电子产业。 当年我国航天工业急需的大规模集成电路,之前全靠进口,一台国外设备要一百多万美元,罗健夫的设备成本不到十万,而且制版效率是国外的三倍。 八十年代初我国发射的多枚导弹,里面的核心芯片都用了他的设备制造的掩膜版,这才有了咱们航天事业的早期突破。 现在年轻人聊芯片,总说卡脖子的难题,可他们或许不知道,五十年前就有个叫罗健夫的人,用命为我们撬开了一道缝。他没有留名青史的惊天壮举,只是在实验室里啃着馒头、熬着夜,把国外的技术封锁一点点打破。 医生说他的肿瘤是长期劳累所致,可他住院时最惦记的,是让同事把省下的药留给更需要的人,是临终前交上最后一次党费,是嘱咐把自己的遗体捐给医院做研究。 今天我们用着智能手机刷着信息,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利,不该忘了这个47岁就耗尽生命的普通人。他不是神,只是个在困难面前不肯低头的共产党员,一个把国家需要看得比生命还重的科研工作者。 罗健夫的名字或许会被时光冲淡,但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台机器,更是一种劲头——那种认准目标就拼命干、为国担当不惜命的劲头,这才是中国科技最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