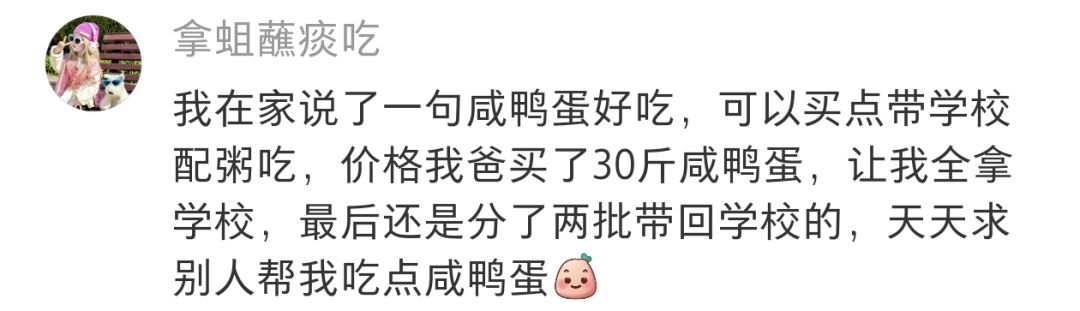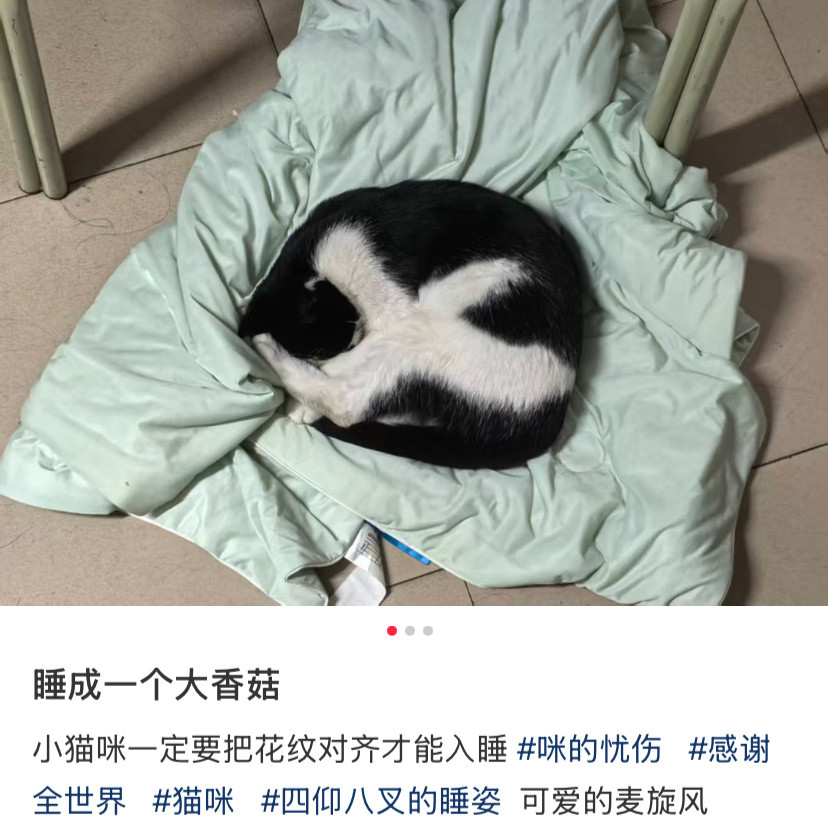酿秋 檐角的玉米还垂着金穗,祖父已把晒透的糯米倒进陶缸。清水顺着木瓢边缘漫开,裹着米粒轻轻翻滚,像把整个秋天的阳光都泡进了水里。 灶台的火塘烧得正旺,松柴噼啪作响,火星子溅在青砖上,转瞬又灭了。陶瓮坐在灶上,蒸汽顺着瓮口的木盖往外冒,混着糯米的甜香,绕着屋梁转了两圈,又从窗缝里钻出去,和院外的桂花香撞个满怀。祖父蹲在灶前,不时用长勺搅一搅瓮里的米浆,勺沿刮过瓮壁,发出沙沙的轻响,像是在和秋天对话。 等米浆熬得稠厚,祖父便把提前备好的酒曲撒进去,指尖沾着的粉末落在米浆里,瞬间融成细小的白纹。他用木勺轻轻拌匀,动作慢得像在呵护易碎的月光:“酒曲要揉进米里,日子才会酿得甜。” 最后,他把拌好的米浆倒进深褐色的酒坛,封坛时在坛口裹了三层油纸,再压上青石板。坛口的缝隙里,偶尔泄出一丝淡淡的酒香,飘在院子里,和晒谷场上的稻草香缠在一起。祖父坐在坛边,摸了摸坛壁,像是在感知时光的温度——要等过了霜降,等坛里的米浆慢慢发酵,等冬天的雪落下来,这坛酒才算真正酿好。 阳光斜斜地落在酒坛上,把坛身的纹路照得清晰。风从院外吹进来,带着秋末的凉意,却吹不散满院的甜香。原来酿酒酿的不只是酒,是把秋天的阳光、祖父的耐心,还有日子里的盼,都封进坛里,等着在某个寒夜,开坛时,满室都是岁月的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