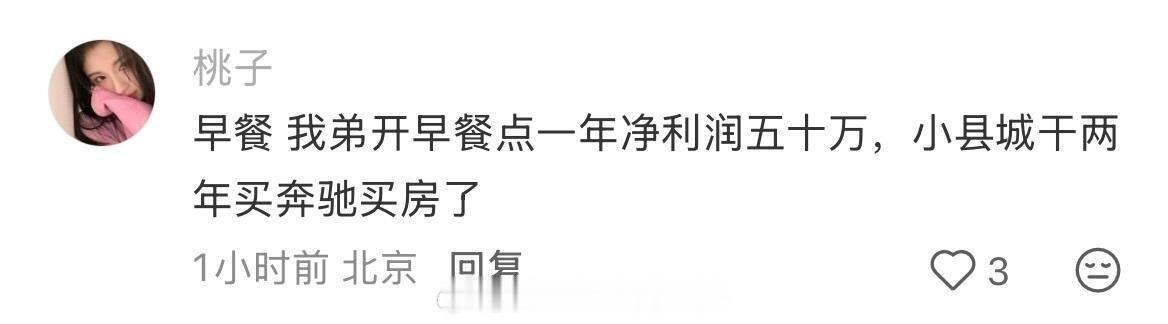1954年冬,我亲手把丈夫送进劳改队,37年后他戴着“特赦证”回家——却把结婚证烧了,说:“桂枝,咱重新拜堂!” 我叫桂枝,娘家是城郊的菜农,丈夫文清是镇上的中学教员。1949年的红绸子还挂在房梁上,字里行间的喜字没褪色,他就被人举报了。 举报信说他曾在民国的报纸上发表过文章,字里行间有“不当言论”。那几天,文清天天被喊去问话,回来就蹲在门槛上抽烟,烟锅子把青石板烫出一个个白印。我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看着他熬红的眼睛,心里跟揣着块冰。 组织上的人找我谈话,说只要我主动揭发,再把他送过去,能算他“坦白从宽”。我整夜没合眼,油灯芯烧得噼啪响,照亮了墙上的结婚证。我知道,我不送他去,他可能会受更重的处分,我送他去,至少能保他一条命。 转天清晨,我把他的铺盖卷捆好,塞进两件我连夜缝的棉袄。他没说话,只是摸了摸儿子的脸,跟着我走了。走到劳改队门口,他回头看我,说:“桂枝,等我。”我点点头,眼泪砸在冻硬的土路上,砸出一个个小坑。 那年我26岁,带着个吃奶的娃,守着三间破土房。街坊邻居有人同情,有人指指点点,说我心狠,说我攀高枝。我不辩解,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地里摘菜,挑到镇上卖,换点粗粮养活儿子。 文清在劳改队的日子不好过,我每年能去看他两次,每次都要走几十里山路,背上背着新做的布鞋、腌好的咸菜,还有儿子写的歪歪扭扭的字。他瘦得脱了形,胳膊上有干活磨出的茧子,却总笑着说自己在里面学了木匠活,等出来给我打个新衣柜。我看着他,想说句软话,话到嘴边却成了“好好改造,我等你”。有媒人上门,说给我介绍个鳏夫,老实本分,能帮我拉扯孩子。 我把媒人撵出家门,关上门就哭。我知道文清没做错什么,他只是生在了那个动荡的年代,读了几本“不合时宜”的书。我守着这个家,守着那句“等我”,一守就是37年。 儿子长大了,考上了大学,娶了媳妇,生了孙子。我从青丝熬成了白发,腰杆也弯了,走路得拄着拐杖。每年去看文清的路,从土路变成了柏油路,我从走路变成了坐拖拉机,后来又坐儿子开的小汽车。他的信从来没断过,字里行间还是当年的温和,只是越来越瘦的字迹里,多了些对岁月的感慨。 1991年的秋天,儿子拿着一封电报跑回家,喊着“妈,爸要回来了!”我手抖得厉害,把珍藏了37年的结婚证翻出来,红绸子已经泛黄,照片上的两个人,笑得眉眼弯弯。 他回来那天,穿了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手里攥着一本红皮的特赦证。他站在门口,看着我,看着院子里的老槐树,看着跑过来喊爷爷的孙子,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儿子媳妇轮番给他夹菜,孙子趴在他腿上撒娇。 饭后,他把那张泛黄的结婚证拿出来,放在蜡烛火苗上。我惊呼着去抢,他按住我的手,说:“桂枝,这张证是年轻时的我们,可这37年,你守着我,我想着你,早就不是一张纸能拴住的了。 咱重新拜堂,拜的是这37年的情分,拜的是往后的日子。”火苗舔舐着红绸子,映得他的眼睛发亮。我看着他,看着跳动的火苗,突然就笑了,眼泪却流得更凶。 那天晚上,没有红绸子,没有唢呐,只有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他对着我,对着儿子孙子,深深鞠了一躬,说:“谢谢桂枝,谢谢你们,等我回家。” 我知道,这37年的等待,不是白费的。那个年代的人,爱得笨拙,爱得固执,爱得能扛住岁月的风霜。一张烧掉的结婚证,烧不掉的是刻在骨子里的牵挂。时代的洪流里,我们都是小人物,却凭着一腔孤勇,守住了最真的情。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