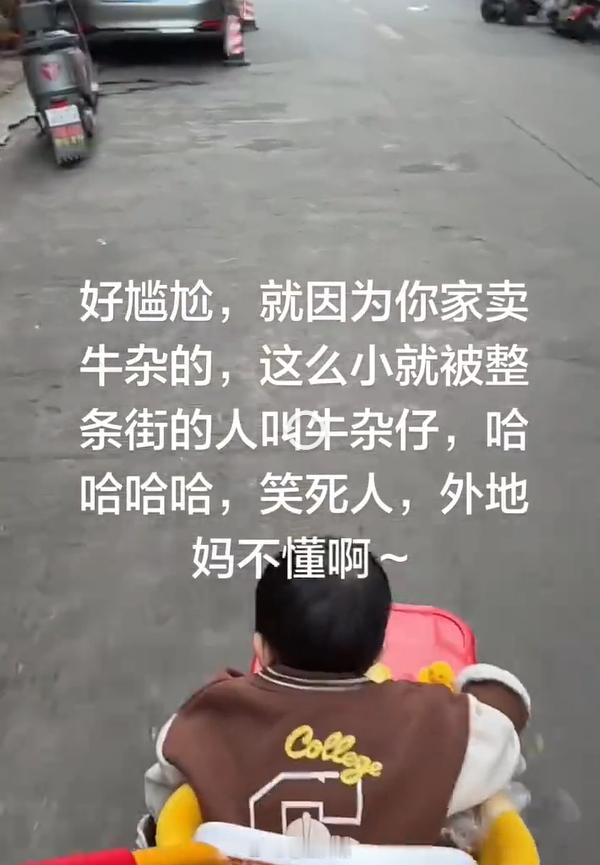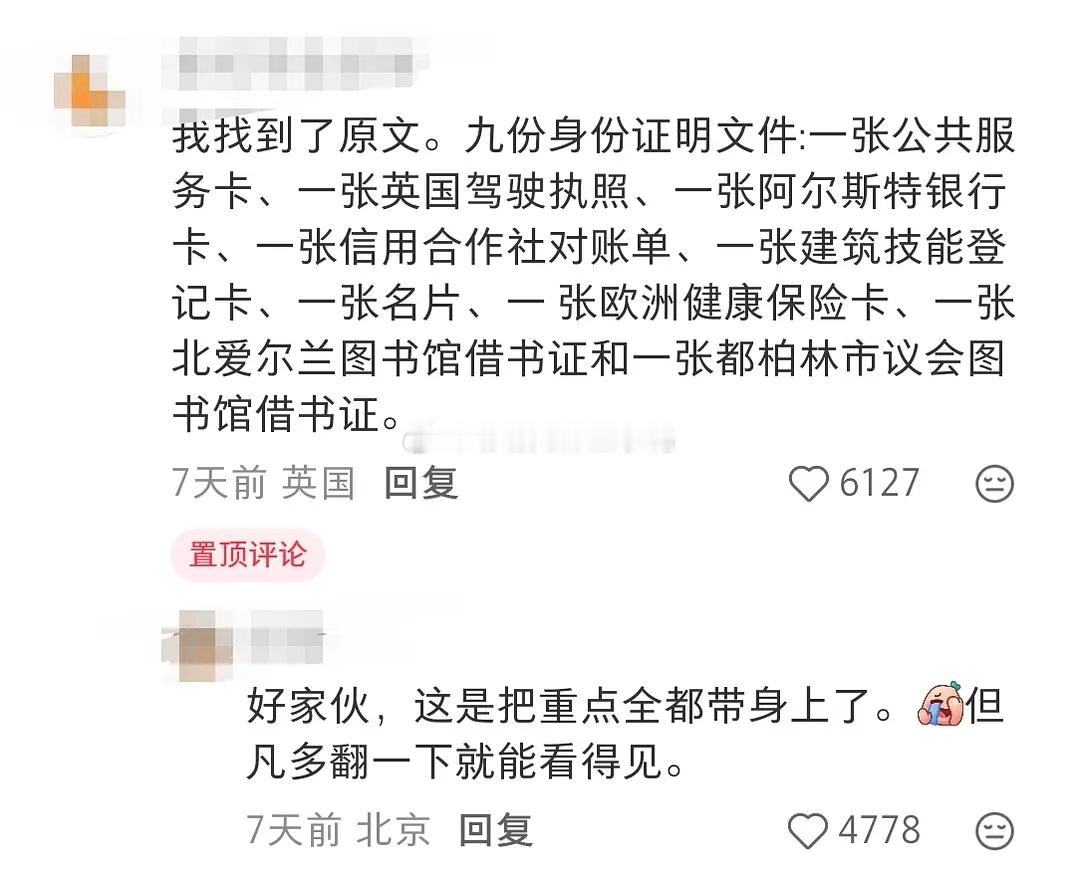1993年,掌握15亿资产的“首富村”大邱庄村支书禹作敏带上一众保镖去市政府开会。而一到场,他就被严阵以待的警察控制。禹作敏瘫坐在地,万念俱灰地说:“我费尽心机,还是失算了。” 1993年4月15日,在天津市政府大楼外,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停下。 车门打开后,被称为“首富村书记”的禹作敏带着保镖下车,神情镇定。 可没人知道,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天。 1930年,天津静海大邱庄的盐碱地里,9岁的禹作敏正赤脚放牛。 风卷起白花花的碱土,糊住他饿得咕咕叫的肚子。 父亲早逝,他啃过野菜,睡过牛棚,却在夜校的油灯下认全了三百个字。 因为,知识是穷人手中 唯一的刀。 1974年,他当上村支书时,大邱庄穷得叮当响。 “靠种地只能喝西北风!” 禹作敏指着龟裂的土地吼道。 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吹到村口,他就带着村民砸锅卖铁凑钱,在铁皮棚里支起第一座小炼钢厂。 炉火映红夜空时,他对工人们喊:“今天流的汗,明天变金砖!” 十年后,大邱庄的烟囱像森林一样竖起来。 钢铁厂、机械厂、运输队遍地开花,村民搬进贴瓷砖的新房,孩子上学有校车接送。 新华社记者挤破头采访,标题全是《从盐碱地到亿元村》。 禹作敏站在新建的办公大楼顶,望着滚滚浓烟得意道:“我这双手,能把荒滩变成金窝!” 钱袋子鼓了,胆子就肥了。 禹作敏把村委会改成“总公司”,自己当“董事长”。 村民私下叫他“土皇帝”,村口设岗哨,外人进门要登记。 厂长必须是亲戚,工人顶嘴立马“喝茶谈话”。 他甚至还组建的保安队荷枪实弹,美其名曰“维护治安”,实为私人武装。 “在咱大邱庄,我说了算!” 某次村民大会上,他拍着桌子训话,“谁不服气,随时滚蛋!” 台下噤若寒蝉。 当年帮他跑贷款的银行行长,如今看他眼神都躲闪。 可权力的毒酒越喝越醉。 1990年冬夜,副厂长因琐事得罪禹作敏的侄女。 他冷笑着对保安队长说:“给他点颜色瞧瞧。” 三小时后,两人被活活打死在仓库。 警察上门调查,禹作敏把行凶者搂在怀里:“我儿子们没错!是他们先动手!” 1992年深秋,外地考察团的车队被保安拦在村口。 “我们犯了啥法?”团长质问。 禹作敏叼着雪茄踱过来:“在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 随后,十几个壮汉把人扣了四小时,直到上级领导来电才放人。 这事没让禹作敏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两个月后,村民危福合在厂里被活活打死。 等到警察带着手铐进村时,禹作敏竟下令:“把警车轮胎扎了!谁敢进来打断腿!” 他站在村口广播站嘶吼:“乡亲们!有人要抢咱们的江山!” 不明真相的村民扛着锄头围住警车,场面一度失控。 “我是大老粗,不懂法律!” 他对着镜头叫嚣,“老百姓也是大老粗,你们硬闯试试?” 这话传到天津市委,领导拍案而起:“无法无天!必须拿下!” 1993年4月15日清晨,禹作敏特意穿上新西装,带着八个保镖去市里“汇报工作”。 “领导要见我,多大的面子!” 他得意地对司机说。 黑色轿车驶入市府大院时,十几名便衣警察从不同方向围上来。 “禹书记,请跟我们走一趟。” 为首的警官亮出证件。 保镖们刚要拔枪,就被特警按倒在地。 禹作敏吓得脸色煞白,突然狂笑起来:“我输了!输给这群穿制服的!” 法庭上,公诉人历数罪状时,旁听席上的村民集体沉默。 那个给他们发电视机的男人,那个盖起教学楼的男人,原来早把村子变成了私人王国。 法官宣判的声音回荡在大厅:“禹作敏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禹作敏入狱第二年,工作组进驻大邱庄。 村民第一次拿到写着自己名字的红本本,房产证。 随后,他们将1800栋新房分到各家各户,厂区烟囱冒的黑烟渐渐变少。 “以前怕他,现在怕没钱。” 老会计蹲在村口抽烟:“禹书记给咱们挣了钱,也差点把大伙儿送进坟里。” 2000年,大邱庄企业改制,随后将集体股份分给村民。 焊管厂、钢管厂的机器声依旧轰鸣,但村口“首富村”的金字招牌早已撤下。 偶尔有记者来采访,白发苍苍的老村民总会念叨:“钱是好东西,可要是掌钱的手脏了,金山银山也得塌!” 历史从不相信眼泪。 禹作敏用二十年把盐碱滩变成聚宝盆,又用权力把这聚宝盆砸得粉碎。 当法槌落下时,他或许才明白:”没有笼子的权力,比野狼更可怕“。 大邱庄的教训刻在法治教材里,也刻在每个村干部心里。 金窝银窝,不如规矩的草窝,金山银山,抵不过法律的红线。 毕竟,能让你站起来的,也能让你摔得更惨。 主要信源:(经济观察报——开放编年史|1993:庄主禹作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