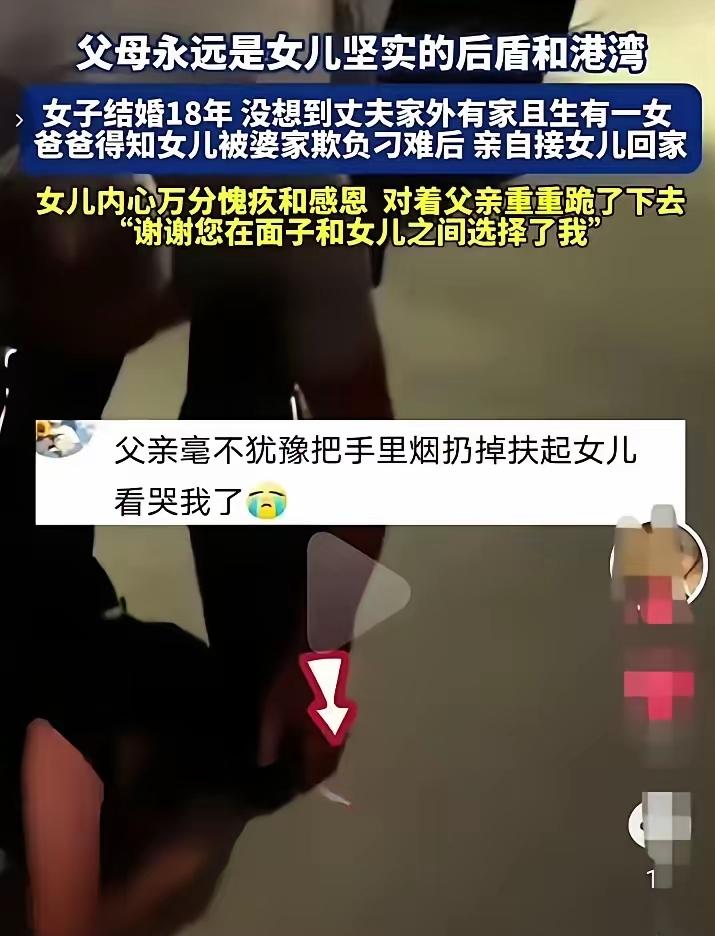1235年,40岁的拖雷在哥哥窝阔台的金帐中饮下了毒酒后,窝阔台便私聊拖雷的妻子唆鲁禾帖尼:“你可愿嫁给我的大儿子贵由,我们强强联手,日后定会战无不胜!” 拖雷走进兄长窝阔台的大帐时,只闻得羊肉膻味裹着马奶酒的酸辛,桌上那只鎏金银盏,杯沿黏着一圈暗红渣滓。 窝阔台说得云淡风轻:“东路军缺主帅,你喝了这杯,明日替我押粮。”拖雷仰头饮尽,不多时咳出一口黑血,洒在羊皮地图上,正好盖住“燕京”二字。很快,他被宣布“暴病身亡”,丧礼从简。 这场“挡灾”的戏码,唆鲁禾帖尼看得比谁都清楚。作为克烈部末代首领王罕的侄女,她太明白窝阔台要什么了。一旦答应改嫁给贵由,拖雷一系的封地、兵权、子嗣,都将顺理成章地被吞并。 她当面只提草原旧规,要先替丈夫净身下葬,又用七天时间,悄悄把佩刀拆段塞进儿子们鞍下,给燕京旧部递去“拖雷死,粮道断”的牙印书信,还把最小的儿子过继远支,先从根子上为这一脉留下一条退路。 这一切,要放回更大的棋盘上去看。成吉思汗晚年立窝阔台为继承人,却把八成兵权交到最宠爱的小儿子拖雷手里,是想用汗位和兵权互相制衡。大儿子术赤因为出身被人疑忌,被远封到西方;二儿子察合台和窝阔台连成一气,两派自此分明。 一边握有“合法”大汗之名,一边掌着实打实的十万精锐骑兵,这种微妙平衡,在窝阔台举起那只银盏时,被彻底打破。 拖雷死后,窝阔台想用一纸婚书,把弟弟留下的势力并到贵由名下,却被唆鲁禾帖尼拖成“一百天守丧”的长线。等到驼队再来,她已带着儿子们迁往克鲁伦河上游,继而投靠术赤之子拔都。 她约束族人,不急着参与汗位争斗,只一味积累战功,因为她比很多男人都懂草原的规矩:忽里台大会看重的,终究还是谁打下的城多,谁带回的财富重。 拔都也在成长。术赤生前被排挤在汗位之外,靠战功和金帐汗国讨回脸面。现在,他带着拖雷长子蒙哥,和老将速不台一道西征,短短六年间连破四个欧洲公国,甚至击败罗马联军,掠回难以计数的财富。 与此同时,窝阔台一系南下攻宋,战线绵长,得地不多,反倒搭上爱子性命,兵力元气大伤。 窝阔台在这六年里荒淫酗酒,最终死在酒后。大汗骤亡,遗命匆忙,只好把汗位交给并不被看好的贵由。照忽里台的老例,要考量前任遗嘱、幼子守灶的传统,也要看候选人战功几何。贵由虽然出身正统,却缺少让全体贵族心服的战绩。 拔都凭借西征赢得的声望,本有资格问鼎,却选择在伏尔加河边搭起金帐,建立自己的汗国,借明退实进的姿态,摆脱了对大汗的绝对从属。 贵由难以容忍这种“阳奉阴违”,点兵亲征拔都,却还没走到对方阵前就病死途中。至此,窝阔台一脉先后经历伐宋不利、大汗早逝、新汗暴毙,势力节节退缩。反倒是当年被他们视作绊脚石的拖雷家族,在唆鲁禾帖尼的布局之下,一点点把失去的话语权夺了回来。 关键的一步,又落在忽里台大会上。拔都本人无意回去争汗位,但他忘不了拖雷生前的照拂,也记得唆鲁禾帖尼提前示警贵由出征的那份情分,于是在大会上力挺蒙哥。1251年,蒙哥登上蒙古大汗之位,黄金家族最高权力,终于转到了拖雷一支手中。 成吉思汗曾经把十万精兵交给小儿子,是押注,也是考验。拖雷用一杯毒酒替兄长“挡灾”,似乎走到了棋盘的尽头。可唆鲁禾帖尼接过这步烫手的棋,用七天、一百天的拖延,把儿子们送到拔都身边,又用克制、战功与远见,换来了蒙哥继位、忽必烈南下建元、旭烈兀西征立国的格局。 窝阔台在酒杯里下过的毒,最终毒死的不是拖雷一脉,而是他自己的后代和苦心经营的汗国。帝国的版图被分割成金帐汗国、伊利汗国、元朝等几块,黄金家族各走各路。 回望这一切,你会发现,那只倒进拖雷喉咙的银盏,真正翻转的,是整个蒙古帝国的方向,而握着盏沿、硬生生把局面拖出新路的,是那个在雪地里拉着遗体、用血为丈夫指路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