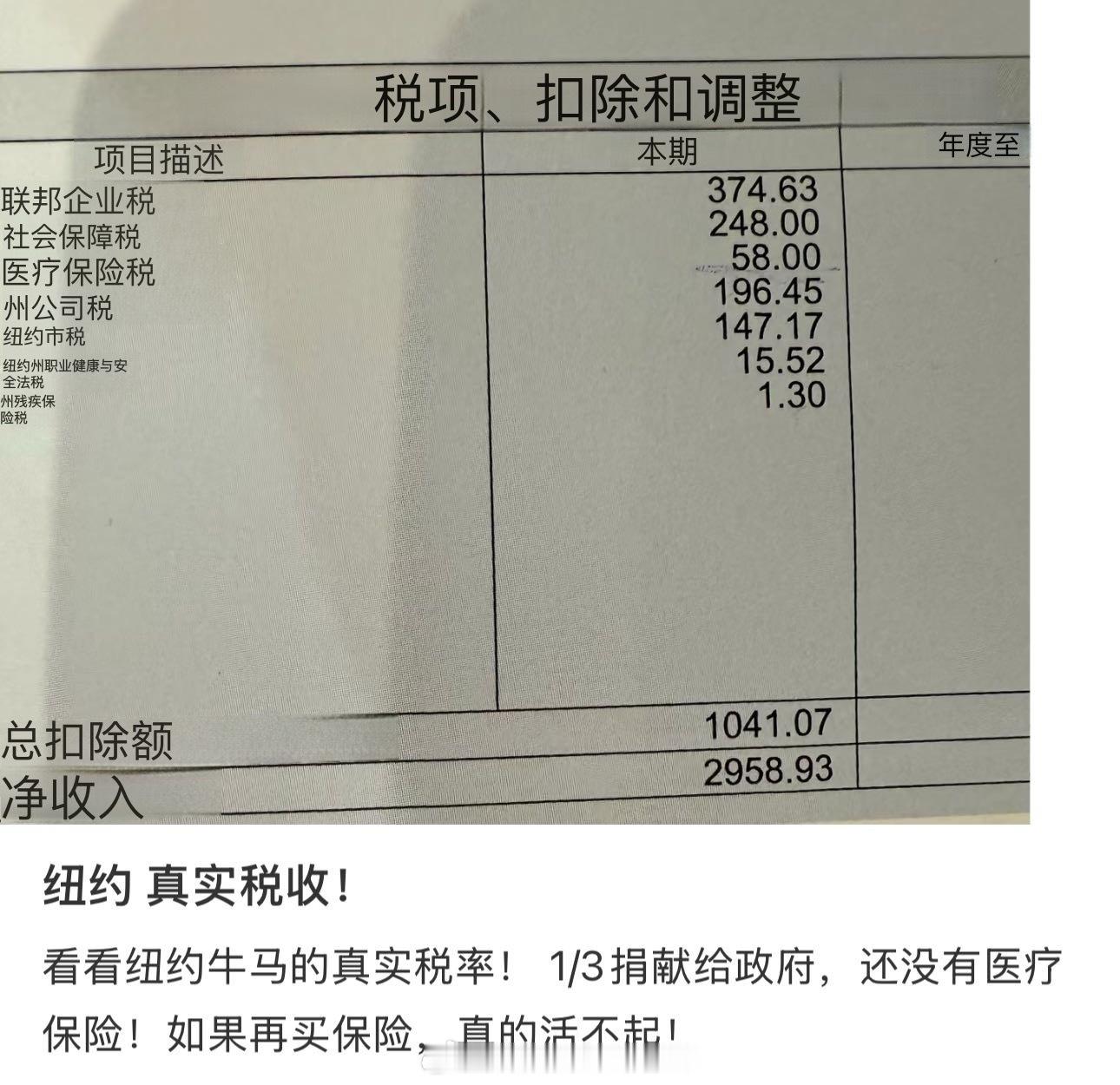哑巴媳妇能说话了,赵老三却再没听她喊过一声“哥”。那年冬天的红薯面早见了底,连带着最后一口暖乎气,也消散在往后的日子里。 土炕还在,铺着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褥子,针脚磨得发毛,像谁反复摩挲过的痕迹。我爷说,林老师(他们后来都这么叫她)刚来时,夜里总坐炕沿上写字,煤油灯的光映着她的手,冻裂的口子渗着血,墨水混着血丝往下淌,在糙纸上洇出暗红的花。 吉普车是七六年秋天来的,黑漆掉了一块,露着底下的铁皮。司机敬礼时,手套磨破的洞露出半截指头,林老师拎着个旧帆布包上了车,没回头。我爷没上车,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明明灭灭,像在数车轮碾过的土,一下,又一下。 他后来开货车跑北京,话越发少了。有次我扒着车窗看,听见他对着后视镜练“你好”,字音生涩,练了三遍,又猛地把镜子转过去,盯着前方的路,不说话了。 林老师在县中教语文,批改作文时总在“平凡”底下画两道线。她左手小指有点弯,是当年咬舌根、说不出话时落下的毛病。 去年翻老柜子,摸出个搪瓷缸,底儿用铁钉刻着“赵老三 云”,字歪歪扭扭,像是拼了全身的劲,硬压进铁皮里的。缸壁上留着一道褐渍,是当年的红薯面汤浸的,洗了多少年,也没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