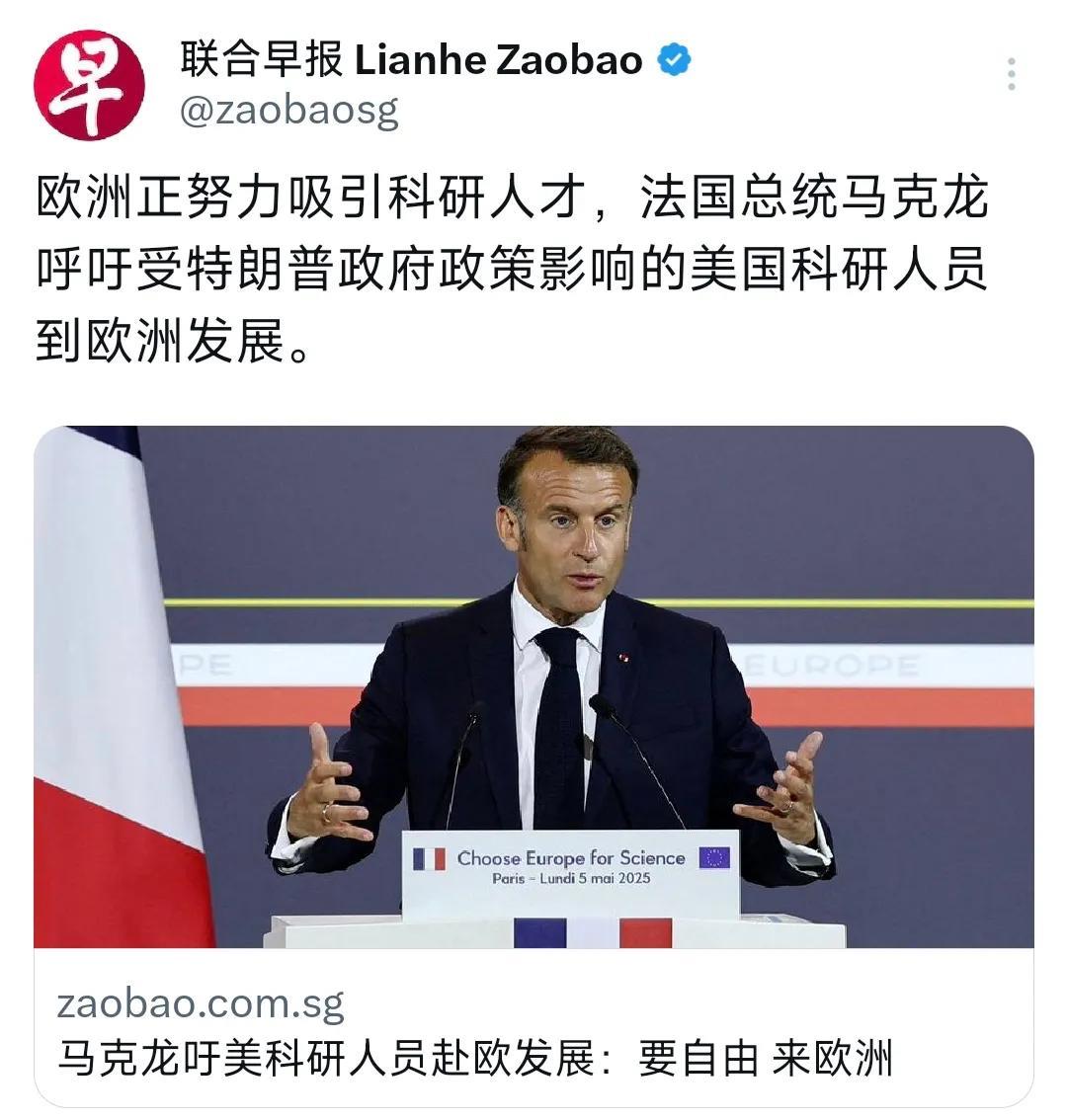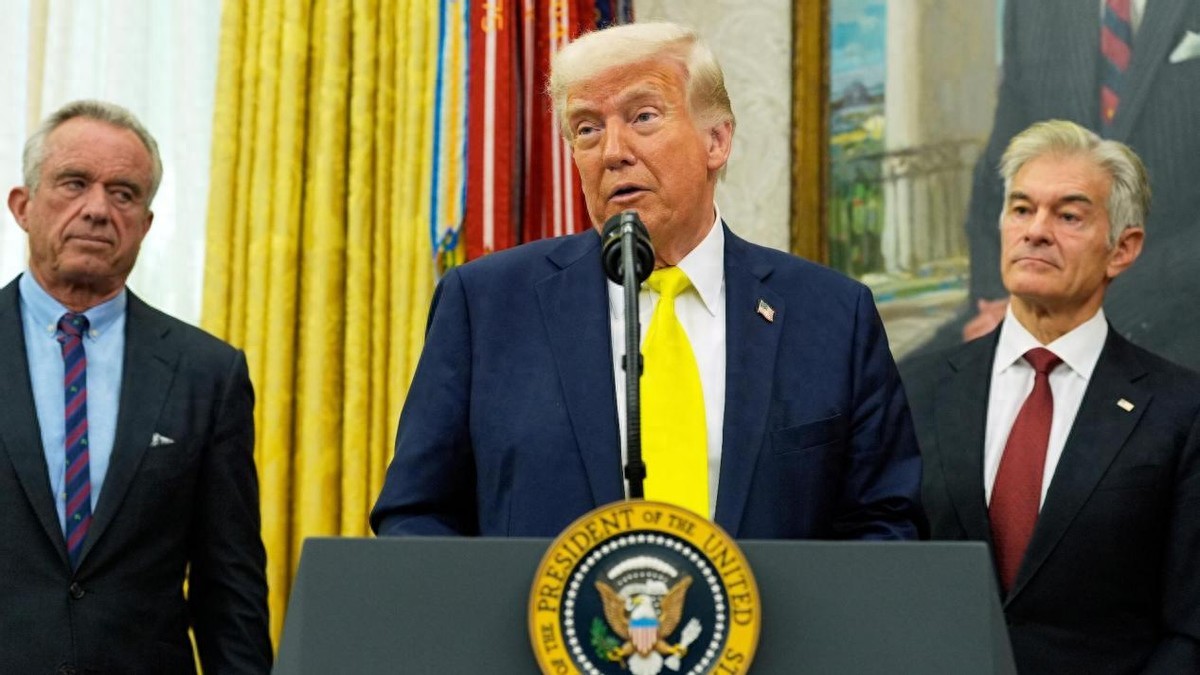澳大利亚刚刚举行了一场重要的大选,总理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以“碾压性”的巨大优势赢得大选。对于很多国际观察人士而言,这是一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选举结果,澳大利亚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重要了?
其实变重要的不是澳大利亚,而是这次选举意味着西方阵营又出现左转的趋势。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在这次选举中一举夺下联盟党多达11个国会席位,加上绿党和独立党的3个席位,在国会中的席位超过了80席,远超半数的76席。这是澳大利亚近年来罕见的碾压局,阿尔巴尼斯也成为21年来首位成功连任的澳大利亚总理。 工党的胜利并非偶然。过去三年,阿尔巴尼斯政府在经济、外交和社会政策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他推行减税、能源补贴、租金援助等政策缓解民生压力,2024年GDP保持1.3%的增长,同时在外交上修复了与中国的关系,成为自2016年以来首位访华的澳大利亚总理。 但这次选举在选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阿尔巴尼斯的民调并不乐观。由于澳联储连续加息、通胀高企、房价飞涨,许多选民对工党的经济治理能力产生怀疑,反对党领袖达顿一度在民调中领先。 但转折点出现在2月。特朗普政府开始对全球盟友挥舞“关税大棒”,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多个国家被加征钢铝关税。阿尔巴尼斯政府试图谈判,但特朗普拒绝豁免澳大利亚。这一事件让澳大利亚选民对特朗普的厌恶情绪迅速升温。洛伊研究所4月的民调显示,68%的澳大利亚人认为特朗普对澳大利亚不利,仅有36%的人相信美国会在全球采取负责任行动。
这不是“特朗普效应”第一次影响西方选举。就在4月28日,加拿大自由党领袖马克·卡尼在选举中击败保守党,成功连任总理。而保守党原本在民调中领先20个百分点,却在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甚至扬言“加拿大应成为美国第51个州”后,支持率暴跌。 澳大利亚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选民对特朗普的厌恶情绪直接转化为对达顿的不信任。阿尔巴尼斯在竞选期间多次强调,达顿若上台,澳大利亚将走向“美式政治分裂”,而工党才是稳定和理性的选择。这一策略奏效了。 过去两年,西方国家的右翼势力似乎势不可挡。德国选择党、英国改革党、法国国民联盟等极右政党纷纷崛起,这些政党多多少少都与特朗普有某种联系,或至少在外交政策上倾向于亲近美国。但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让美国变得“人嫌狗厌”,与他的关系反而成了右翼政党的“支持率毒药”。 达顿就是典型案例。他原本希望通过模仿特朗普的强硬风格吸引选民,甚至在加沙问题上称赞特朗普是“伟大的交易者、思想家”,甚至表示自己愿意成为“澳大利亚的特朗普”。但在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引发众怒后,达顿的支持率迅速下滑,他试图在辩论中与特朗普切割,称“我不认识特朗普,从未见过他”。 虽然这个滑跪很丝滑,但为时已晚,澳大利亚选民并不买账。他们担心,如果达顿上台,澳大利亚可能会被卷入更激烈的美中对抗,甚至沦为地缘冲突的前线,所以联盟党这次输得特惨。相比之下,阿尔巴尼斯虽然也强调美澳同盟,但至少在外交上保持了相对平衡的姿态,这让选民觉得更安全。
但也有人记得,在竞选期间,阿尔巴尼斯曾放话,如果连任,将“收回”中国企业租赁的达尔文港。这一表态引发外界猜测:他是否在向美国示好?还是单纯觊觎港口的收益? 达尔文港是澳大利亚北部的重要战略港口,2015年由中国岚桥集团以5亿澳元获得99年租赁权。尽管2023年澳政府的审查未发现安全风险,但部分政客仍坚持要求“回购”。阿尔巴尼斯的表态可能是为了争取国内民族主义选民的支持,但实际操作上,他不太可能采取极端措施。 原因很简单:阿尔巴尼斯能逆转选情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选民希望他能在中美之间找到平衡,而不是彻底倒向美国。如果他真的撕毁达尔文港协议,不仅会损害澳大利亚的商业信誉,还可能引发中国的反制,影响正在复苏的澳中贸易。2023年以来,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已恢复至60亿澳元,葡萄酒、龙虾等产品重新进入中国市场。阿尔巴尼斯不会轻易破坏这一局面。
在经济上,他可能会继续推动减税和住房政策,缓解选民的生活成本压力。在外交上,他会深化美澳军事合作,但避免在台海、南海等问题上过度刺激中国。在贸易上,他可能寻求豁免美国的关税,同时维持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但他赢得第二任期后,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的政策将更加灵活,既不会完全追随美国,也不会彻底倒向中国。 对中国来说,需要做好预案,既要应对可能的达尔文港争议,也要抓住机会扩大经贸合作。未来几年,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可能会更加务实,而中国也需要以更灵活的方式应对这一变化;其实我们从来不怕对手务实,只要不是当年莫里森那样的一根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