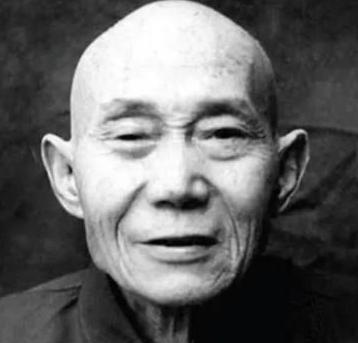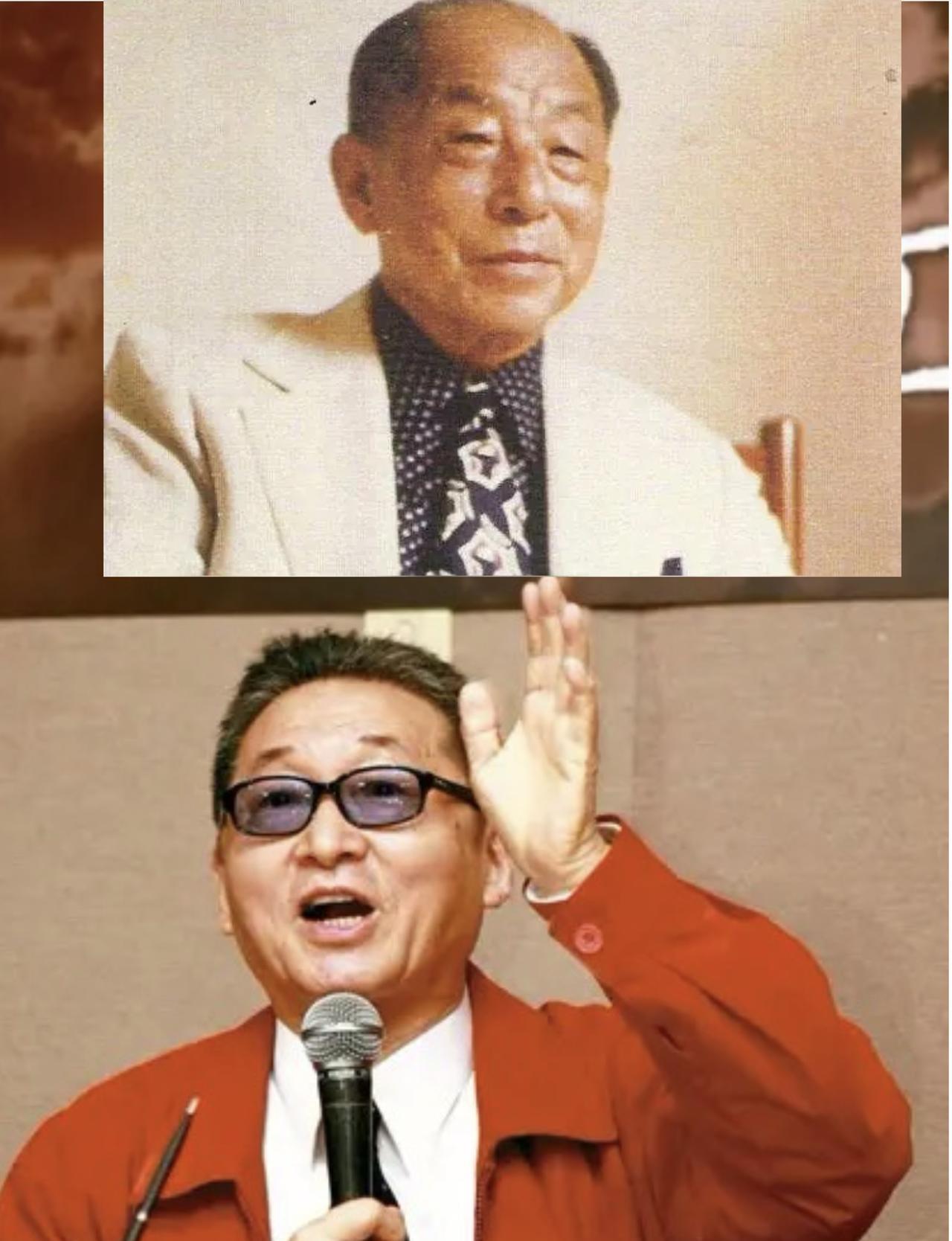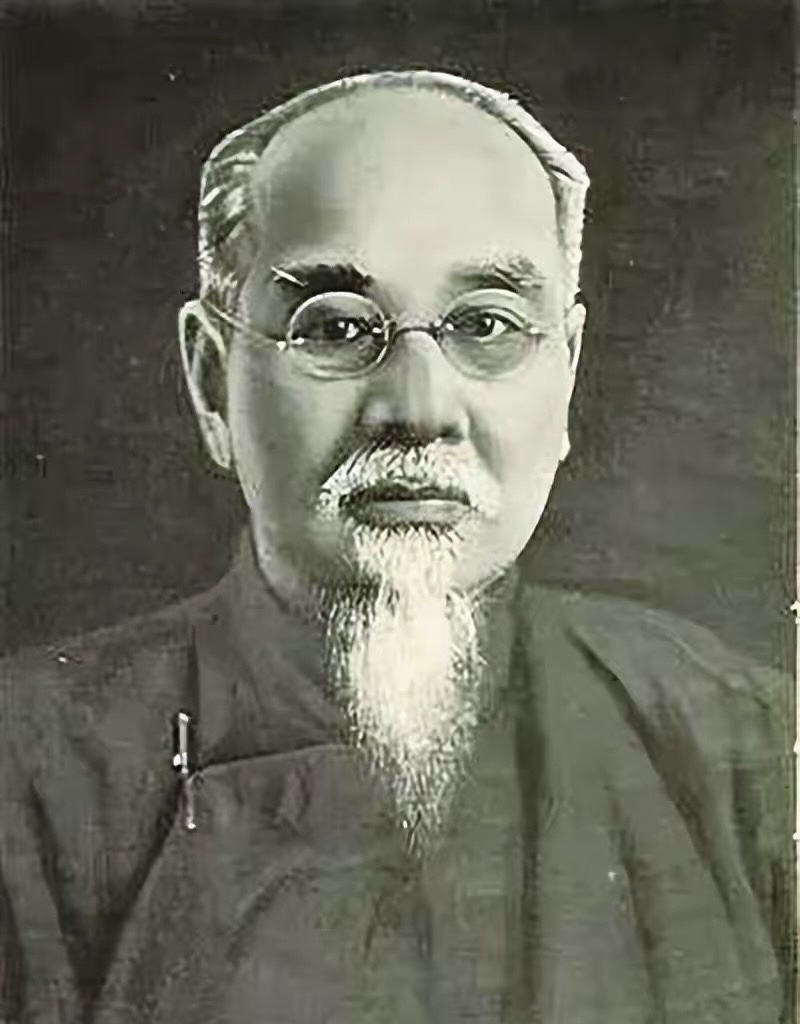1937年,马步芳草拟了两份电报,准备调兵遣将围剿红西路军。电报员曾庆良看到内容时,脸色大变,因为曾庆良原来也是红军! 1937年3月,那会儿西路军经历了几个月的血战,被打散了,剩下由李先念带着的一千多人,是最后的火种。他们正准备翻越祁连山,往新疆走,寻找生路。老蒋和马步芳当然不干啊,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马步芳亲自草拟了两份“十万火急”的电报,一道发给驻西宁的马步銮旅,一道发给在河西的骑兵总指挥马彪,命令他们一个北上堵截,一个就近围剿,形成一个天罗地网,要把这支孤军彻底捏碎。 这两份电报,经过加密,火速送到了西宁总电台。接电报的是报务主任熊维邦。这位熊主任,业务熟练,但有个小爱好——新婚燕尔,心思总往家里跑。他瞄了一眼电报,看是加急的,也没细看内容,顺手就交给了替他值班的曾庆良,自己拍拍屁股回家了。 就是这个“顺手”,给了历史一个拐弯的机会。 曾庆良拿到密码稿,一看内容,瞬间头皮发麻,手脚冰凉。电报上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颗射向自己同志的子弹。这电报一旦发出,李先念那支队伍,可能就真的走到头了。 发,还是不发?这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这是一道生死题。发,对不起自己的信仰和同志;不发,马步芳的手段,他见识过,那绝对是生不如死。而且,他当时在西宁已经找到了失散的妻子,妻子还怀着身孕。一边是家,一边是国,一边是小爱,一边是大义。 他没有声张,也没有犹豫太久。他走到发报机前,像往常一样,手指在电键上飞舞,发出一连串“滴滴答答”的声音。给外人看,他正在忙着发送这份十万火急的军令。但实际上,他发的可能只是一段乱码,甚至什么都没发。演完这出戏后,他悄悄地把那两份要命的电报稿,放回了熊维邦的办公桌上,然后像个没事人一样,下班回家。 这一放,就是四天。 四天后,马步芳的电话打爆了电务处:为什么马彪的部队还没动静?前线刘呈德的部队已经跟红军在玉门青山头交上火了,说好的合围呢? 这下炸了锅。电务处处长赵焕耀、电台台长张之俊,火急火燎地找到熊维邦。熊维邦冲进机房,一眼就看到了自己办公桌上那份“熟悉的”电报稿,还静静地躺在那儿。他当时魂儿都快吓飞了,一把揪过曾庆良:“这电报你怎么没发?!” 曾庆良的反应,堪称影帝级别。他一脸无辜又带着点惶恐,解释说:“主任,那天机器干扰太厉害了,信号时断时续,我试了好几次都发不出去,想着等会儿再试试,后来一忙就给忘了……” 这理由,搁现在咱们听着都觉得扯。但在当时,熊维邦他们,竟然就这么信了。或者说,他们选择了相信。 这里头的事儿就更有意思了。熊维邦、张之俊这几个人,他们心里难道不怀疑吗?张之俊就嘀咕过:“准是曾庆良他们有意扣下了电报。”赵焕耀也附和:“这是一封命令追击他们西路军的电报呀。”他们门儿清! 但为什么没人捅破这层窗户纸?说白了,是怕担责任。如果把曾庆良是“内鬼”这事儿上报,马步芳固然会宰了曾庆良,但他们几个用人失察、监管不力的罪名也跑不了。熊维邦玩忽职守是板上钉钉的。所以,几个人一合计,干脆就坡下驴,把锅甩给了“天气不好,信号干扰”。他们跑去跟马步芳汇报,说反正前线已经打上了,您老人家对老蒋那边也算有交代了。 马步芳这个草包,竟然也就这么被糊弄过去了。 一个英雄的壮举,最终能成功,除了英雄自身的勇敢和智慧,有时候还需要对手的愚蠢和自私来“配合”。熊维邦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无意中成了曾庆良的“同谋”,共同完成了一次对历史的“拯救”。 后来呢?曾庆良的身份并没有暴露。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被俘的西路军人员有了重获自由的机会。曾庆良在被押送途中,瞅准机会成功逃脱,回到了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他凭着自己的技术和贡献,一步步成长为我军通信领域的专家,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而他当年冒死救下的那支部队,在李先念的带领下,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抵达新疆,为后来的革命保留了宝贵的火种。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电报员,在历史的岔路口,用一次“不作为”,撬动了历史的走向。这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永远不要低估一个普通人在关键时刻所能爆发出的能量。宏大的历史叙事,固然是由伟人们引领,但最终构成历史血肉的,正是无数个像曾庆良这样,在自己的战位上,做出了无愧于心选择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