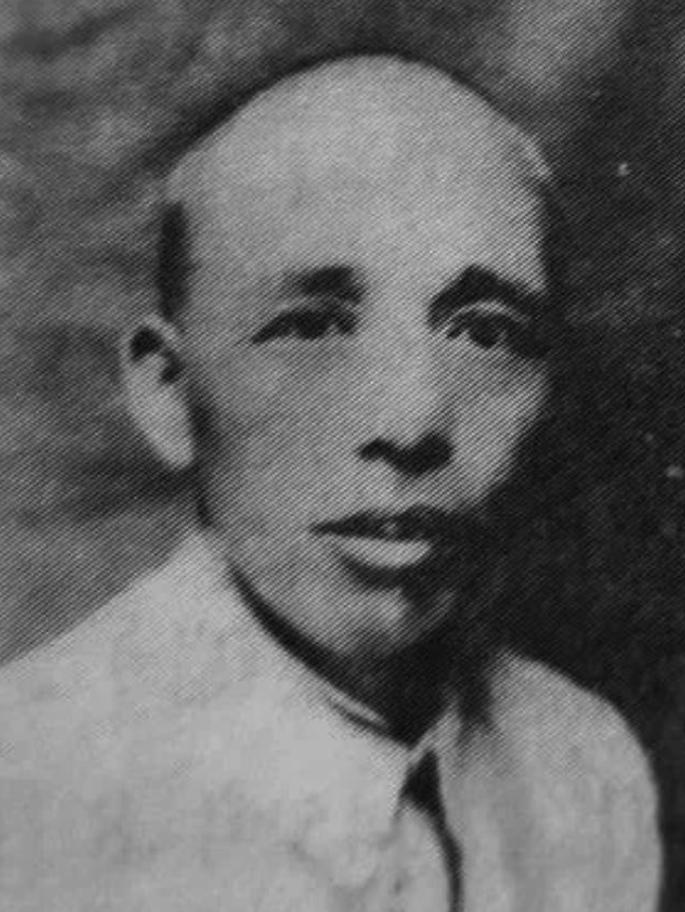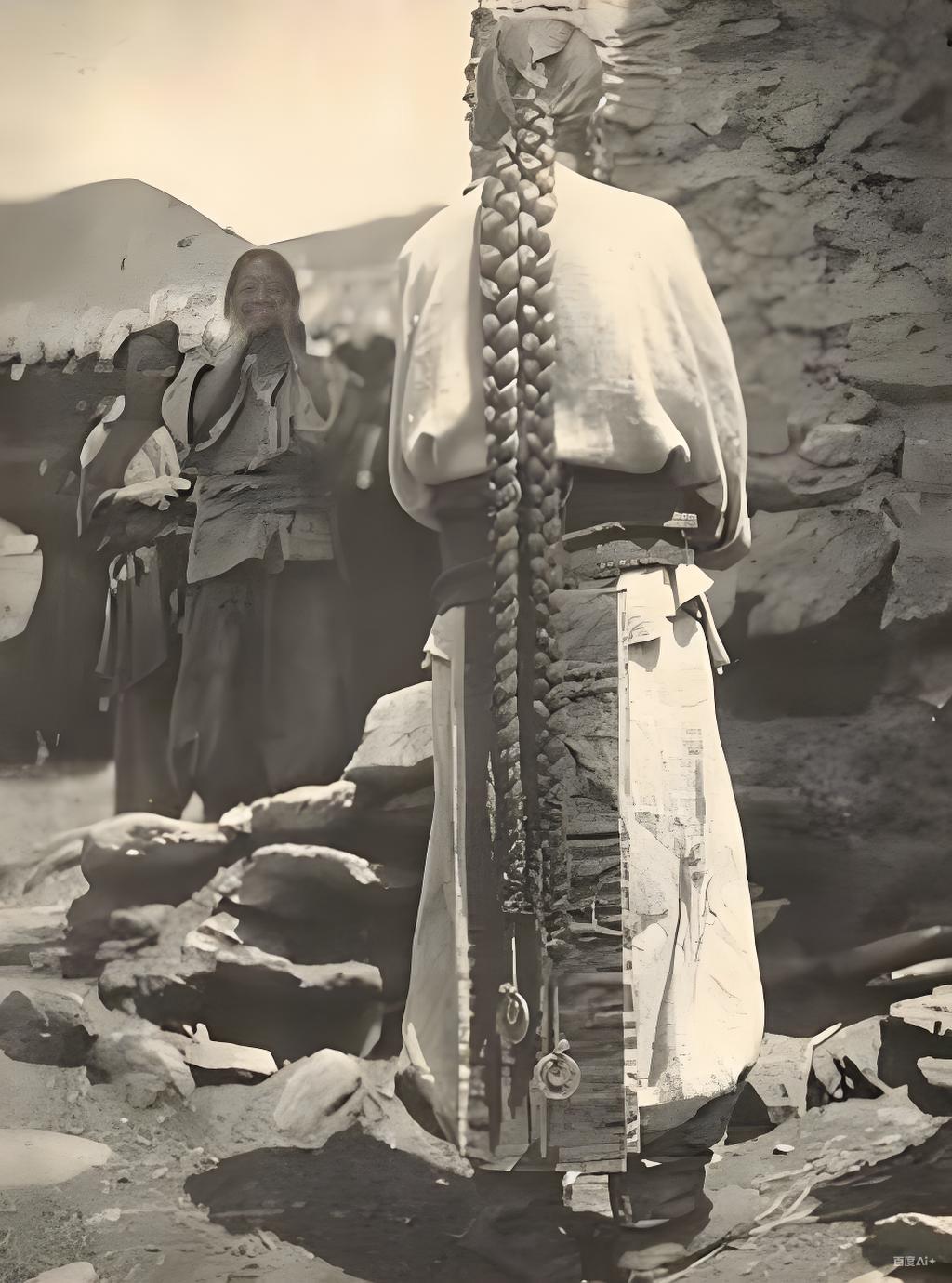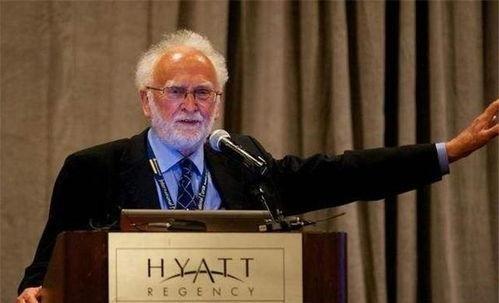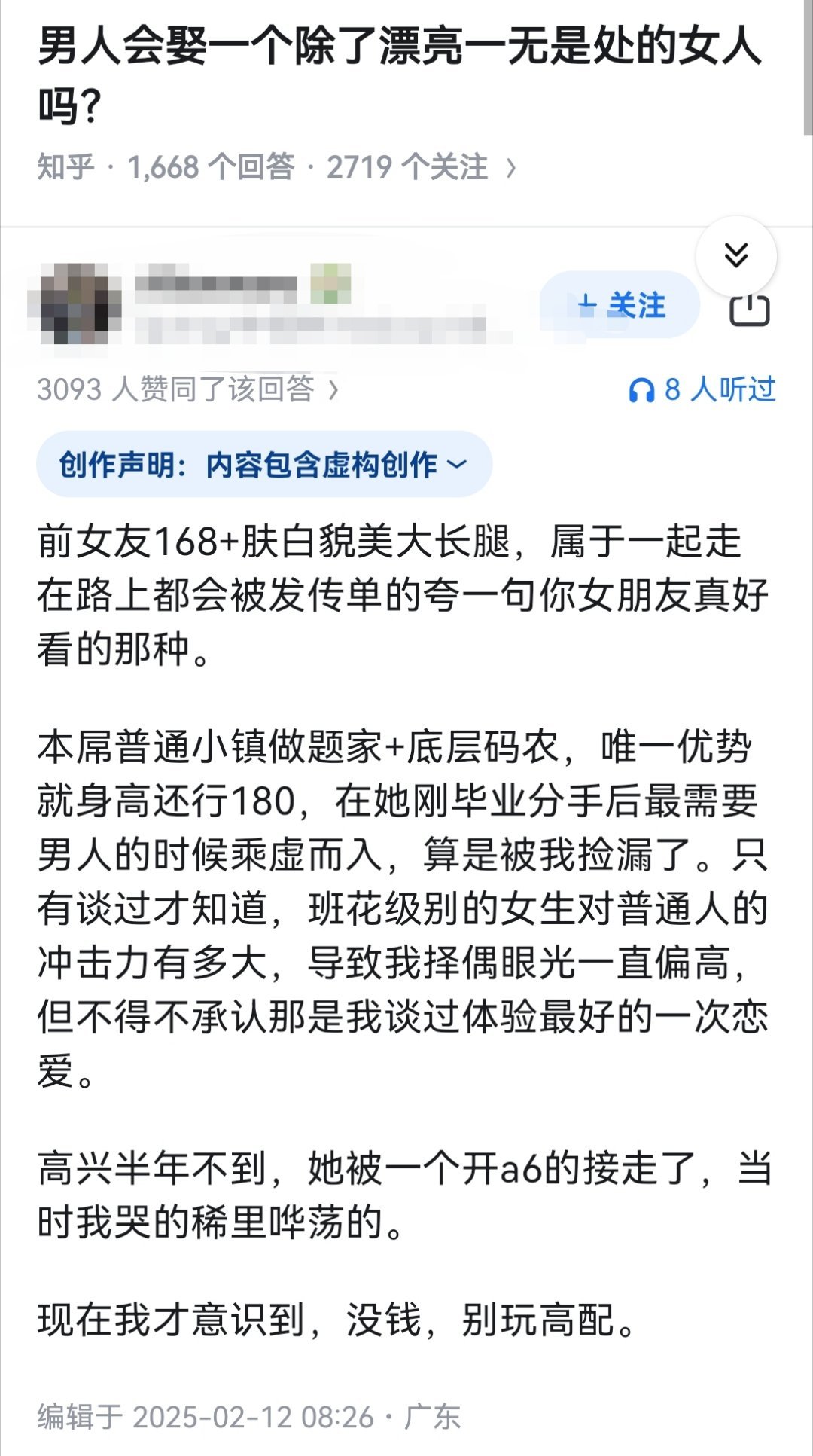冯唐:我贪财好色!当妇科医生,就是为了光明正大地看女人! 冯唐本名张海鹏,1971年出生在北京,父母都是工厂技术员。 他从小成绩就好,高考时本来有保送北京医科大学的机会,但母亲问协和是不是更好,他就又复习了半年,1990年19岁考进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读8年制临床医学,专攻妇科肿瘤方向。 很多人把他这句玩笑话当真,其实他在《有本事》里早就说透了真实原因——就是想“以毒攻毒”改掉自己好色的毛病。青春期的他对异性充满好奇,翻遍《曾国藩家训》后受了启发,曾国藩用忙工作转移注意力,他就想干脆钻进女性患者最多的妇科,天天面对专业场景,反而能脱敏。 而且他选妇科肿瘤可不是随便选的,同班同学龚晓明后来爆料,冯唐那时候好胜心极强,认定协和妇产科是全国最好的科室,非要进这个顶尖领域证明自己。90年代的协和8年制有多难读?前两年要在清华修完数理化、文史哲通识课,后六年专攻医学,还得闯过中期考核的淘汰关,当时顶尖院校的淘汰率约15%,博士阶段还得发表SCI论文才能毕业。 他在北京东城胡同长大,小学四年级数学考砸过,却偷偷琢磨家里《黄帝内经》里“恬淡虚无”的意思,这种对知识的钻劲,让他在协和硬生生泡了八年。每天不是泡图书馆抄病例,就是跟着朗景和、沈铿这些泰斗级导师学手术,光手写的肿瘤病例笔记就攒了十几本,后来《万物生长》里的医学细节,全是这段日子的真实写照。 1998年他27岁博士毕业,直接留在协和妇科肿瘤科当医生,每天早上八点准时查房,管的三十多张床位里,大多是卵巢癌患者。那些日子他见了太多残酷场景,患者化疗后脱发呕吐,腹部肿块大到影响生活,他亲手记录了287例晚期癌症病例,还发现83%的卵巢癌患者都有“遇事自己憋着”的习惯。 那会儿男性做妇科医生比现在难多了,就像同期的男妇科医生何涛说的,病人见了男医生扭头就走是常事,有的家属对外介绍都含糊说“是外科大夫”。冯唐也没逃过这种偏见,刚上临床时,有患者一看见他是男的,二话不说就退号,还有人私下议论他“动机不纯”。 但他没当回事,一门心思扑在诊疗上。按医院规定,男妇科医生看病必须有第三方在场,他就主动请护士全程陪同,用专业打破顾虑。那些年他几乎是三点一线,查房、手术、写病例,有时候忙得一周都见不到太阳,可从没抱怨过一句。 谁也没想到,当了三年医生他会辞职。不是因为受不了偏见,而是见了太多晚期患者的无奈,他开始质疑自己的选择——就算技术再精湛,也拦不住很多癌症的进展。这种无力感让他纠结了很久,最终决定换条路走。 但协和八年没白待,他记录的病例、培养的严谨思维,后来全派上了用场。去美国读MBA拿了托福满分,进麦肯锡七年做到全球合伙人,后来当华润医疗CEO收购四家公立医院,再到中信资本负责医疗投资,始终没离开医疗领域。 那些嘲笑他“贪财好色”的人,根本没读懂他的自嘲。90年代社会对男妇科医生的偏见有多深?有年轻男性直接觉得这行是“耍流氓”,可冯唐用三年临床经历证明,医生眼里只有病人没有性别。他后来总结的“5分钟情绪熔断法”,其实最早就是在病房里练出来的——面对患者的痛苦和家属的焦虑,得先让自己冷静下来才能救人。 他的经历其实藏着一个时代的变化,90年代初妇产科医生短缺,却没多少男性愿意涉足,冯唐这样的先行者,用自己的选择打破了职业性别壁垒。现在越来越多男妇科医生被认可,不就是因为他们像冯唐当年那样,靠技术和责任赢得了信任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