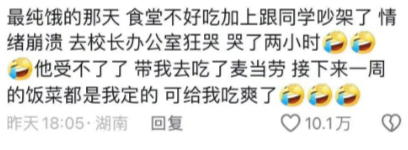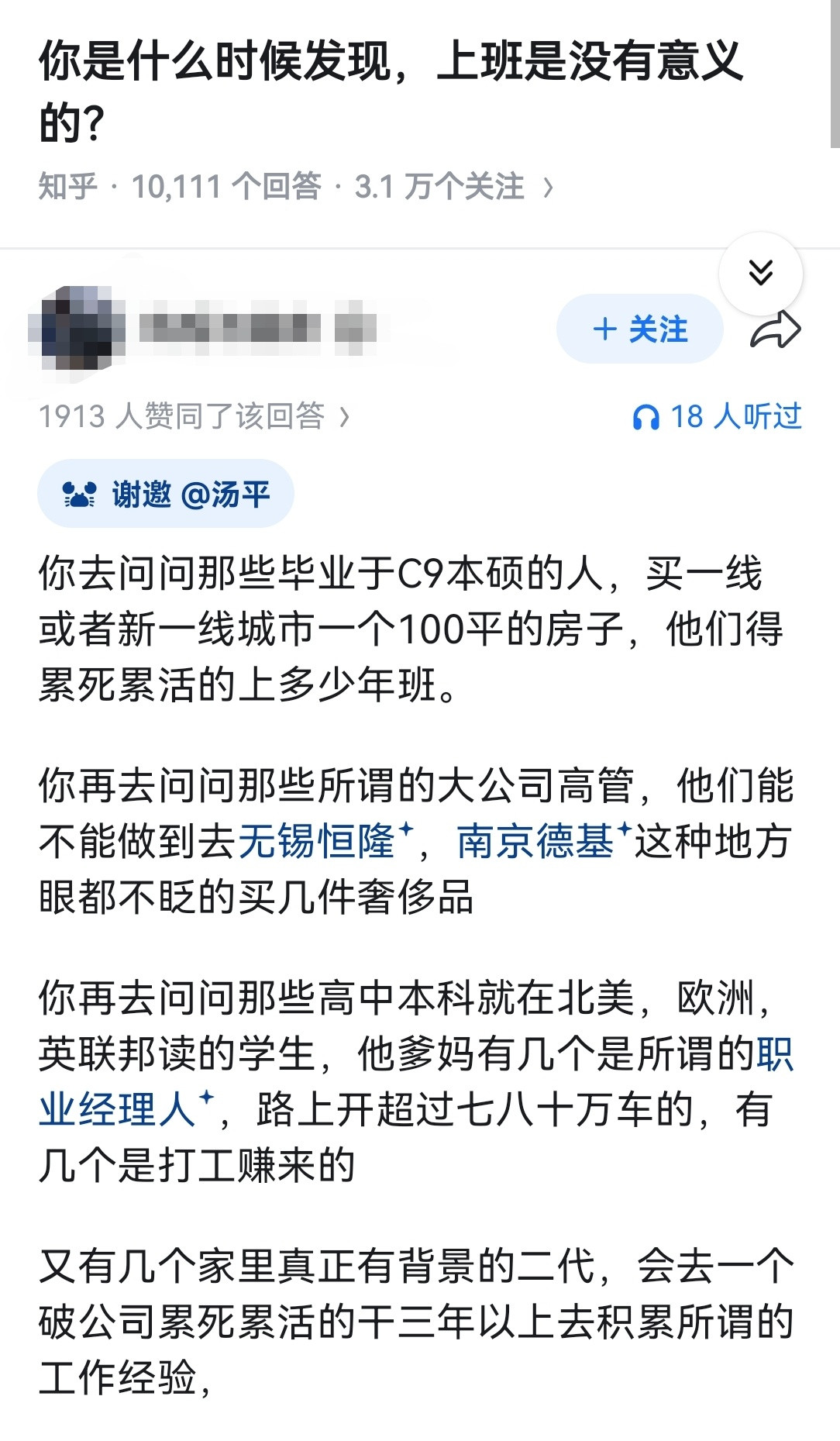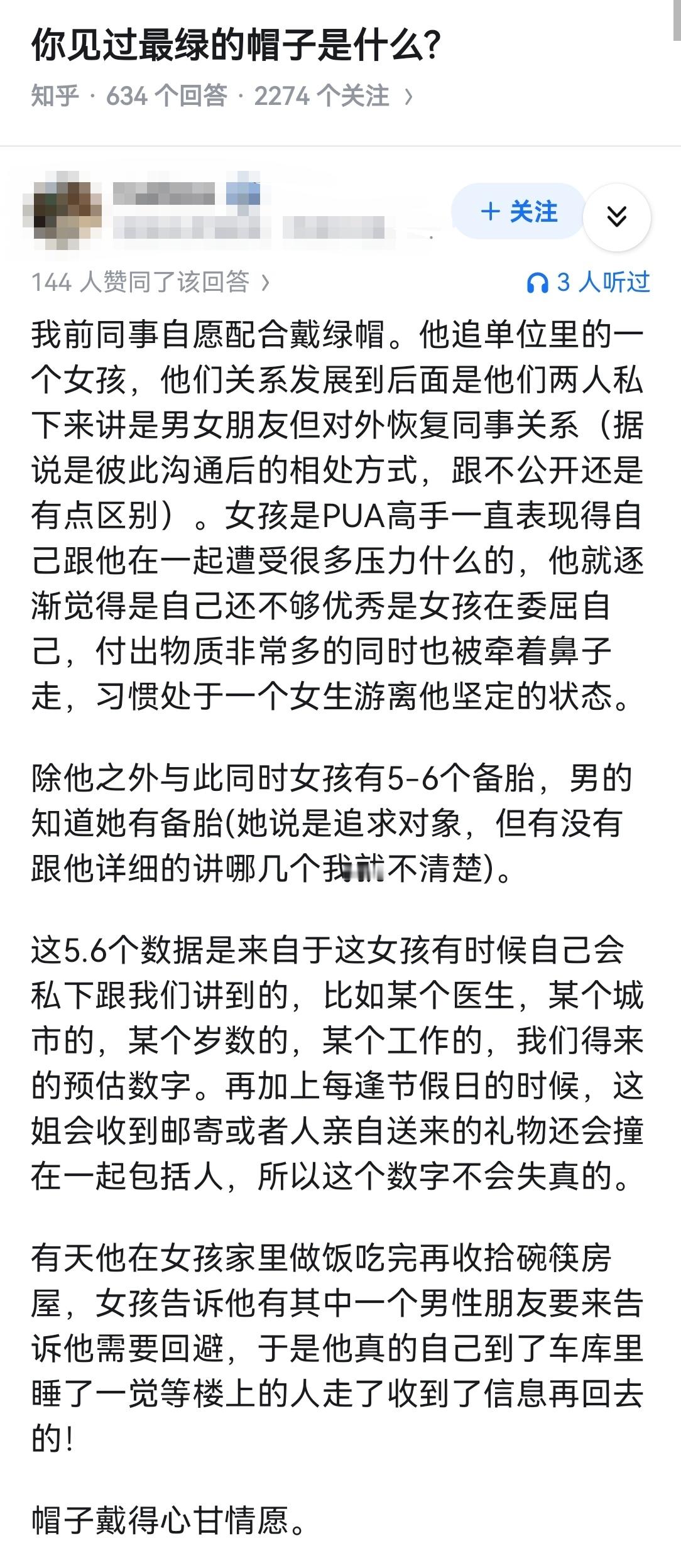六十年代末,伯父要分家,他说伯母身体不好,不能生气,就把奶奶分给我们家。每天清晨,我妈洗漱完,先打扫院子,再去厨房忙活一家人的早餐。那时候粮食紧张,玉米面掺着红薯面蒸的窝头是主食,偶尔能喝上玉米糊糊就算改善伙食。 六十年代末的北风刮过胡同那天,伯父蹲在院里石磨上抽烟。 烟蒂烫出第三个小洞时,他说分家吧——伯母身体不好,受不得气,奶奶得跟你们过。 我扒着门框看,奶奶坐在灶门前的小马扎上,手里的火钳把灶膛里的火星拨得一闪一闪,没说话。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妈就起了床。 她先拿起扫帚,把院子扫得没有一片落叶,连墙根下的鸡粪都用碎土盖得严严实实;再进厨房,灶台边的水缸结着层薄冰,她哈着白气舀水,哗啦一声倒进锅里。 奶奶的铺盖卷儿被我爸扛进西厢房时,她摸了摸炕席,又摸了摸窗台,最后把一个蓝布包塞进枕头底下——后来我才知道,里面是她攒了半辈子的几块零钱。 我妈每天的日子像上了弦的钟,洗漱完就扎进院子,扫完地就进厨房,锅碗瓢盆的声响里,天一点点亮透。 那时候粮食金贵得很,玉米面掺着红薯面蒸的窝头,硬邦邦的能硌掉牙;偶尔熬一锅玉米糊糊,就算是改善伙食,我和弟弟能把碗舔得比脸还干净。 我妈总把窝头蒸得稍微软和些,第一锅出锅,先捡两个最大的,用干净布包着,端进西厢房给奶奶。 有天我起夜,看见奶奶站在厨房门口,背对着我,手里攥着个窝头往我妈兜里塞,我妈推了回去,两人小声说着什么,灶台上的油灯把她们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两棵挨得紧紧的树。 直到那年冬天最冷的一个清晨,我缩在被窝里听厨房动静,听见我妈哎哟一声,跑过去看见她蹲在地上,手里捏着个热乎的窝头——是奶奶趁她扫院子时,偷偷把自己那份窝头揣在怀里捂热了,想让她先垫垫肚子,结果手滑掉地上了,黄澄澄的渣子撒了一地。 你说那时候粮食那么紧张,一个窝头恨不得掰成四瓣吃,她怎么就舍得把自己那份捂热了给别人呢? 后来我长大些,在粮站排队时听见隔壁大婶说,伯父家那几年确实难,伯母常年喝中药,堂哥刚上学又总生病,或许他说“受不得气”,不全是托词,只是那个年代的人,连说句“我也难”都觉得丢脸。 我妈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只是每天清晨雷打不动地早起,扫院子时会特意把西厢房门口的雪扫得宽些,蒸窝头时会多掺一勺热水,让面发得更暄乎点;奶奶也没说过一句感谢的话,只是从那天起,我妈兜里偶尔会多出颗糖——是她走亲戚时藏下的,用皱纹纸包了三层,糖纸都被体温焐软了。 奶奶在我们家过了整整十五年,走的时候很安详,手里还攥着我妈给她做的蓝布帕子。 很多年后我自己成家,在厨房蒸馒头时总想起那些掺红薯面的窝头,才明白:日子再难,只要心里装着人,硬邦邦的窝头也能捂出热气,就像冰天雪地里,两个人的影子挨得紧了,就都不觉得冷了。 你看,所谓亲情,不就是有人愿意早起扫雪,有人愿意藏起糖块,在稀松平常的日子里,把彼此的难处悄悄往自己肩上扛一点吗? 前几天整理老照片,翻出一张泛黄的黑白照,我妈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扫帚,身后西厢房的门帘掀开一角,露出奶奶的半张脸。 照片里的天也是蒙蒙亮,像极了那个清晨,灶台上的窝头冒着热气,把整个屋子都熏得暖烘烘的——那香味,我到现在都记得。
我嫂子性格很奇怪,她今年55岁了,每天我哥上班以后,她就门一关,基本不出门,最久
【6评论】【14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