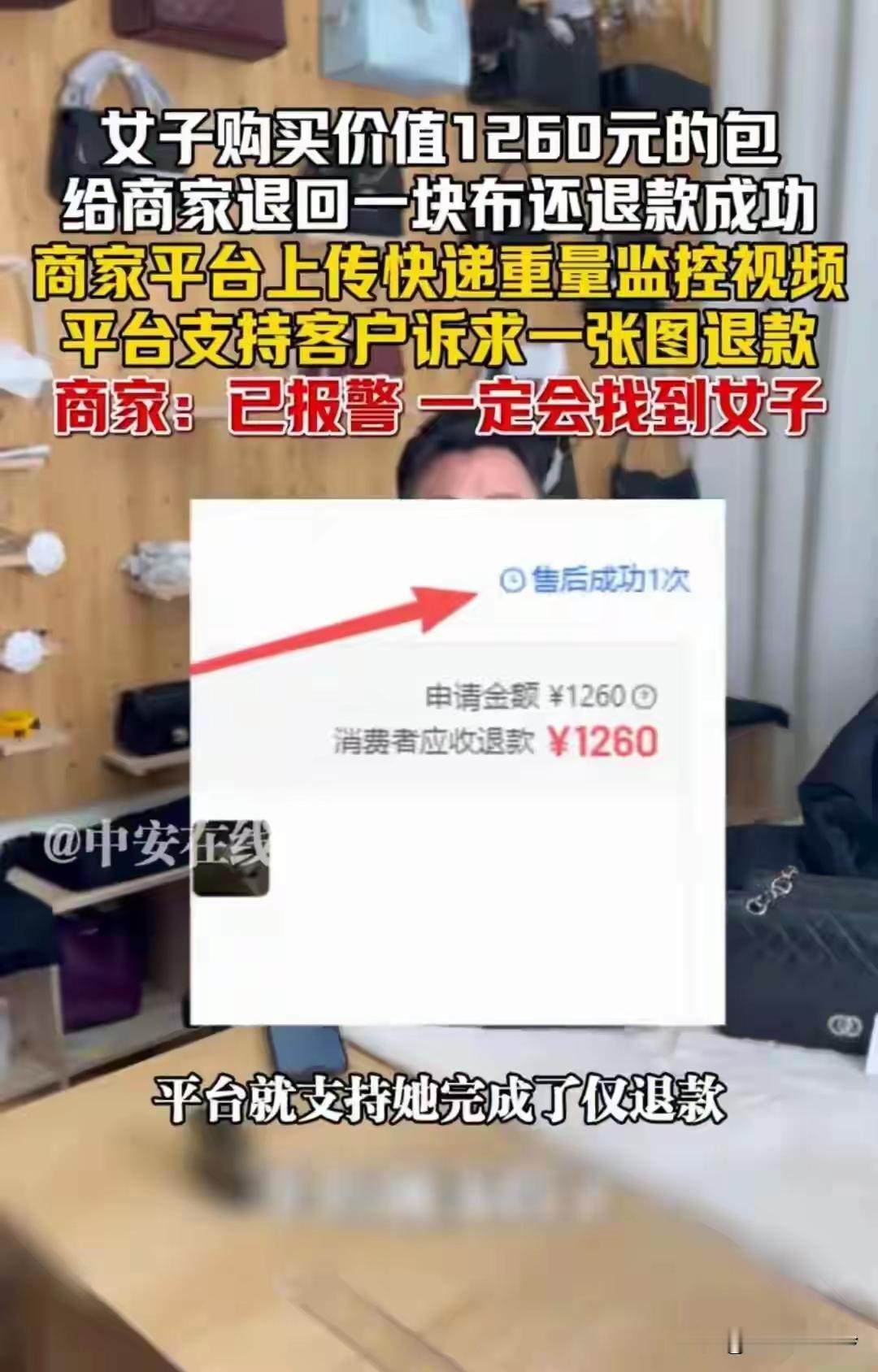今天一大早,我和丈夫就赶回30多里以外的农村老家。老房子是80年代初建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行,一般家庭盖房子都没有全部用砖的,都是起地以上1米用砖,然后上面就是用的粘土泥和碎麦杆合起来的土胚块,我们这儿叫“积块”。 今天一大早,我和丈夫就往30多里外的老家赶;车轮碾过柏油路,又颠过一段坑洼的土路,空气里渐渐漫开麦秸秆和湿泥土的味儿。 到了院门口,老房子还是老样子——青灰色的砖从地基垒到齐腰高,再往上,就是土黄色的“积块”,表面坑坑洼洼,像爷爷手上皲裂的皮肤。 80年代初盖房时,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买整面墙的砖,父亲带着几个叔伯,在麦收后晒透了碎麦秆,和着刚翻出来的粘土泥,一锨锨拌匀,脱成半人高的积块,码在院子里晒足七七四十九天,才敢往墙上砌。 那会儿我总蹲在旁边看,觉得那些土块丑巴巴的,哪有别人家砖房好看? 这次回来,丈夫伸手摸了摸积块墙,指腹蹭下一点干土,“你看这纹路,还能看出麦秆的碎渣呢。” 我凑近了闻,土腥味里混着淡淡的霉味,倒比城里的消毒水好闻——那是小时候下雨时,墙皮渗水后晒干的味道,多少年了还没散。 我们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堂屋里光线暗,阳光从木格窗斜斜照进来,落在墙角的旧木箱上;箱子是母亲当年的陪嫁,上面还贴着褪色的“囍”字,旁边堆着我小时候穿的虎头鞋,鞋底磨得快平了,鞋面的老虎眼睛却还亮闪闪的。 忽然注意到西墙根,积块上有个浅浅的小坑,像被什么东西砸过;猛地想起十岁那年,我和邻居家小妹抢皮球,失手把搪瓷碗摔墙上,碗没碎,墙却凹进去一小块,父亲当时气得要打我,母亲拉着说“孩子皮,墙结实着呢”——原来这坑,它一直替我记着那天的哭闹和母亲的笑。 以前总觉得这土胚房寒酸,比不上同学家的砖瓦房;可现在摸着这些积块,倒觉得比钢筋水泥暖和——砖是冷的,土是活的,里面藏着父亲脱坯时的汗,母亲晒麦秆时的念叨,还有我一整个童年的吵闹。 那会儿家里穷,盖房只能“半截砖半截土”,可正是这省钱的土办法,让我们在每个下雨的夜晚,能缩在被窝里听着雨点打在积块上“沙沙”响,知道屋顶不会漏,墙不会塌。 日头爬到头顶时,我们准备回城,回头望,老房子的砖基在阳光下泛着青,土黄色的积块墙却像裹了层柔光;车轮重新碾过土路,可麦秸秆和湿泥土的味儿,好像还粘在衣服上,洗不掉了。 下次回来,该带把小刷子,把积块墙上的浮土轻轻扫扫,别让那些麦秆的碎渣被风刮跑了——它们和那些旧时光一样,都是老家给我们留的念想啊。
当我回家晚了,妈妈在电话里骂我
【1点赞】